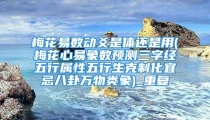北宋景祐三年(1036),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天是苏东坡的诞辰。为让更多人了解苏东坡的心迹历程,惠集读书社特刊发小草先生的作品《苏东坡:余生正是重生时》。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饮东坡醒更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苏轼在黄州写的一阕词好《临江仙.夜归临皋》。词里写了苏轼夜深宴饮归来,已是三更,童仆深睡,敲门不醒,他只好独自倚着藜杖倾听江水奔流的涛声,然后生发出一番感慨:常恨躯体不属于我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忘却为功名利禄而奔竞钻营!不如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坦平,驾起小船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此词融叙事、抒情及反思人生于浑然一体,令人喜爱。然而我最关注的是词中结句出现的“余生”字眼。所谓“余生”,通常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晚年,二是指大灾大难后侥幸保存的生命。苏轼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贬黄州,时年45岁。此词写于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年47岁。显然,47岁即使在古代也不应该算是晚年,苏轼的“余生”想来应该是第二层意思,即“乌台诗案”后侥幸保存的生命。我还注意到,贬居黄州的苏轼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的“余生”或“余龄”。在他的《江城子》一词中,“余龄”这个字眼同样出现在结句之中: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急,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层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此词也是苏轼47岁时所作,即与《临江仙》词是同一年的作品。他在词中把东坡雪堂比作陶渊明的斜川,“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苏辙语)。苏轼在此词中不仅使用了与“余生”同义的“余龄”一词,而且更为直白、更加强烈地感叹自己“吾老矣”。此时此刻,他仍旧是在黄州,仍旧是在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仍旧是只有47岁,但感叹人生老矣的语气似乎更为沉重了。再进一步阅读苏轼在黄州贬居期间的诗文,会发现更多与其“余生”、“余龄”意思相近或相关联的语句:侄子安节来黄州看望苏轼,他言自己“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一》)“残年”不就是“余生”、“余龄”吗?且由“残年”想起风烛残年、残年馀力等成语,总是溢漫那种无助、无奈而悲凉之感。苏轼在黄州写的《次韵前篇》诗中感叹:“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哪禁泻”。他叹息未来的一切都不可预期,自己的“余年”似酒那般不禁泼洒。“余年”显然是“余生”、“余龄”的另外一种表述。苏轼给侄子安节的诗中还有“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唯应识旧声”之句,其笔下衰老、羸弱、瘦硬的个人容貌令人惊心骇目,以至侄子只能凭不变的乡音来相认了。这是“余生”、“余龄”令个人容貌衰老、形象变异而留下的痕迹。蜀僧明操思归,苏轼赋诗云:“更厌劳生能几日,莫将归思扰衰年。片云会日元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这诗意既是劝慰亦是自慰,诗中“衰年”无疑也是“余生”、“余龄”的同义词,而且体现了“余年”衰老之特征。元丰六年(1083)三月,苏轼久病,令其身体与心境大受影响,有诗句“我今老病不出门”、“门外桃花开自落”(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芙蓉仙人(石景卿也)旧游)。他久病积弱,连近在自家门边的桃花都懒得去看了,任其自开自落。此时苏轼自叹不仅“老”,而且“病”,乃“老病”之人也。总之,黄州贬居期间的苏轼,认定自己已经进入了“余生”,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余生”以及与“余生”同义、近义的词如“余龄”、“余年”、“残年”、“衰年”、“老病”写进了自己的诗文之中。他在黄州写的第一阕叹息“余年”的词是贬居此地的第三年,但所谓“余年”并非独指当年,而是指自己45岁罪谪黄州以后的这些岁月,都属于“余年”。除了苏轼的自述,在别人的传闻与描述中,贬居黄州的“东坡居士”也是一副“余生”衰貌。金代元好问在《赤壁图》诗中称苏轼为“憔悴黄州一秃翁”,头发脱落严重。苏轼在黄州时期又卧病家中,一春未出,以至“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因误传苏轼与曾巩同日病逝,有人准备前去吊恤和周济苏家。二.当年曾“城上结庐亲指顾,敢将忠义折狂澜”45岁这个年龄,原本不应该成为正常人生的“余生”,更何况是苏轼。苏轼并非平庸之辈,无论是在考场还是在官场,也无论是在文坛,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令人仰望之人。在45岁之前,他风华正茂,锐意进取,经受历炼;在45岁之时,他年富力强,厚积经验,正待大用,岂会黯然进入自己的“余生”呢?这完全不在其人生发展的正常逻辑之内和世人对其的普遍期待啊!苏轼21至22岁时,就成为大宋科考场上一鸣惊人、名震天下的骄子。他与弟苏辙先是在开封府的进士考试中双双入选,然后又通过了礼部考试,其成绩获第二(因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此文为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所作,出于避嫌而将本该名列首位的文章改为第二);其后礼部进行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获得第一。苏轼兄弟表现出的才华令欧阳修十分喜爱,他对苏轼更是赞不绝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更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轼26岁时,就成为制科考试拔得头筹的“百年一人”。制科考试乃“天子之命为制”,是宋代宝塔尖式的人才遴选,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非进士考试可以比拟。宋朝三百多年间,共录取进士四万余名,而制举考试总共才举行二十二次,人等者即成绩合格者仅有四十一人,与进士录取率有千倍之差距。制举考试成绩一等、二等为虚设,三、四等为实设,三等实则是第一等(三等又有三等、三等次之分)。这次制科考试苏轼荣摘三等,成为宋朝开国百年来入三等第一人,故被誉为“百年一人”,无冕之王也。苏辙也获得四等。兄弟俩的才华与气质令仁宗皇帝激奋不已,回宫后对皇后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就在这一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这大概相当于北宋前期进士科状元的待遇,他从此踏上仕途。王安石在其任职敕书中撰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这个未来成为苏轼最大政敌的人,当时在敕书中居然对他如此激赏、褒奖、勉励,夸耀毫不吝啬,推举不遗余力,或许是兼有皇帝授意与王安石本意吧。苏轼33岁时,就成为天子御试的考官。考官虽然级别不一定高,但要求必须科举进士出身,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是令人敬重的角色。那年是熙宁三年(1070),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这是一场以广开言路、改善治政为目的考试改革。这次考试,苏轼担任考官,他发现专考策论异化为专媚时君的不良风气,愤然上书皇上,又借用此次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深入剖析策论考试异化之弊,引起皇帝的关注与重视。翌年苏轼34岁,得到皇帝单独召见倾听其对改革之看法。出道初期的苏轼主要在朝廷大理寺等机构供职,虽然职位尚低,但他能够站在治国谋政顶层设计的高度,向朝廷呈上制策,希望对已经显露危机的北宋王朝作出自己的贡献。神宗皇帝让苏轼“坦白指陈,无须避讳”,苏轼也抓住这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向皇帝陈述了自己对改革、对治国谋政重大问题的想法与建议,令皇帝印象深刻。不久他又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皇帝本想起用他,可惜苏轼毕竟太年轻,缺乏城府,走漏了皇帝召见的风声,使皇帝拟起用他的安排受到了阻挠而未实现。苏轼36岁时,因无法接受王安石的激进新法,自请离京城任职,到地方历炼。苏轼虽然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决策的顶层设计,甚至连对顶层设计的影响力都被阻隔了,受到了堪称当头一棒的打击,然而他并未因此消极、沉沦。苏轼先到杭州做判官,然后到密州、徐州、湖州担任太守,主政一方。他是从40岁开始担任地方主官的。他在地方任职共八年两个月,每到一地无论时间长短,都有所作为,政绩斐然,深得民心,广受爱戴。尤其是他在密州和徐州担任独挡一面的地方长官时,在复杂局面与突发事件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其爱民情怀和果敢的工作能力,为北宋政坛带来了一股清风,亦为自己树立了形象,建立了威望。苏轼最难忘的应该是,他到徐州上任四个月后就遇上了历史罕见的一场洪灾,他临危不乱,“城上结庐亲指顾,敢将忠义折狂澜”(道潜诗),成功地组织民众和协调驻军打了一场抗洪大仗,三年后苏轼调离徐州,父老乡亲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他们或遮道拦马,苦苦挽留;或洗盏呈酒,致谢感恩,然后流泪追送数十里。苏轼从府试中举到湖州履新,即从21岁到45岁间的24间,他不仅作为拥有政绩声誉、发展后劲和远大前途的“后备干部”而在北宋政坛引人注目,而且凭其在文学艺术各领域的深厚造诣、卓越才华、渊博学识以及人格魅力,在士林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40岁前后的四、五年里更是如日中天,声名远播,成为广受膜拜的“男神”。他只要写出了什么诗文,乡野城邑、市井朝廷、茶楼食肆,无论何处都能迅速传播,引起轰动;文人骚客、平民高官、僧侣妓妇,无论谁人都是争相吟读,以先为快。甚至神宗皇帝也成为苏轼的超级粉丝,平日最喜欢读他的诗文,每每总是反复阅读,爱不释手,时常会情不自禁地为之击节称叹:“奇才!奇才!”宫中嫔妃都知道神宗皇帝这一癖好,所以只要见他用餐时忽然停下筷子而专注阅读,她们不用猜就明白,这一定是苏轼的文章让他入迷了。如此一个“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人物,苏轼其名若苍穹星辰,熠熠生辉;其前途天宽地阔,未可估量;世人仰之,士林尊之,异邦慕之,太后宠之,皇帝期待之,此时此刻谁会料到他的灾祸竟从天而降,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他的“余生”提前到来了呢?三.乌台诗案的影响: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连苏轼本人也未意识到自己“余生”会提前到来。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此前他已经在多地任职,对地方事务已经如鱼得水,他内心深处虽依然向往参与朝廷决策的顶层设计工作,但也已经喜欢做地方百姓的父母官。他在徐州抗洪有功,获得了神宗皇帝的嘉奖,民望陡涨。他是带着最新的光环来到湖州的,所以自我感觉不错,心情愉悦。初到湖州,他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解州情、访问民众的同时,还利用闲暇与人一起出城看荷花、登岘山、游飞英寺、泛舟清江、瞻仰古贤遗踪等。当然苏轼也没有忘记自己走马上任后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循例向皇帝呈交一份“致谢信”——《湖州谢上表》。这种表章原本就是一份做做样子、表表感恩的报到书,不必认真,敷衍即可。可是苏轼一提起笔来,却管不住自己,他说得太多,说得太掏心,说得太激愤,说得有人对号入座太难受。连最不应该说的话他也说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意思是,臣知道自己笨拙不堪、不合时宜,难以与“新进”们一起陪伴陛下左右;臣已是过了“惹是生非”的年龄,一定会在地方好好干。谁都知道,“新进”一词当时是突然晋升而又无德无能之辈的代名词,是带有污辱性的词语,是当时官场最忌讳的词语,苏轼如此明目张胆挖苦“新进”、嘲讽“新进”,把矛头直指皇帝赏识、提拔、组阁的朝廷百官,孰可忍,孰不可忍?!文份表章让苏轼的反对者又气又喜,气的是苏轼竟敢如此蔑视他们,喜的是他们终于在白纸黑字中找到苏轼“讪谤朝廷”的把柄。苏轼的名气太大,光环太亮,锋芒太露,皇帝对他太喜欢,民众对他太崇拜,反对者对他又妒又恨又害怕,一直都想扳倒他,可苏轼从未贪公帑之一毫,从未办错案之一宗,从未误政事之一桩,从未愧百姓之一人,令他们无从下手。这次终于找到向苏轼开刀的突破口了,政治阵营的敌人,个人恩怨的仇人,见不得人好的小人,以及一切心理阴暗的人,迅速集结,全面行动,对他发起疯狂而猛烈的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的围攻者像打了鸡血那样亢奋,以超出诗人百倍的想象力对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随意曲解,妄加发挥,以寻找罪证,编造罪名。苏轼在那份“致谢信”上表示:“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也被认为这表面上是感恩,实质是提醒神宗皇帝勿忘先帝曾说过苏轼兄弟是宰相之才,不要再将他外放地方为官,让他早日上朝堂辅治天下,是典型的“伸手要官”。总之,苏轼的诗文被他的曲解成一条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的“铁证”,属于罪大恶极,不可饶恕,逼得神宗皇帝不得不命御史台对苏轼立案审查。于是苏轼成为“如驱犬鸡”一样被拉走的罪犯,成为乌台阴暗狭窄牢笼里的囚徒。苏轼认定自己不但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而且性命难保,亡在旦夕,他在一天挥泪写下了予苏辙的诀别诗《狱中寄子由》: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在这首诀别诗里,苏轼跟弟弟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是:为兄未满半百,就已经没有余生,唯希望能有来生,但愿以后世世代代都能与你做兄弟,我们把此生没有了却的因缘都付诸来世吧。此诗凄楚而情深,神宗皇帝看到这首诗后,亦为二苏埙箎之情潸然泪下。神宗皇帝向来欣赏苏轼的才华,也不太相信苏轼有不臣之心,只是想挫一挫他恃才狂傲的气势,从未想过要杀掉苏轼。在民间为苏轼开展的救赎活动方兴未艾的感召下,在少数士大夫不惧株连为苏轼仗义执言的推动下,在太后“不须赦天下凶罪,只放了苏轼一人足矣”之言的触动下,神宗皇帝最终作出处理苏轼的决定:免去死罪,贬去黄州。于是苏轼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重罪不诛,大难不死,自己居然还有“余生”,这完全出乎苏轼的意料。尽管他无法预料自己的“余生”是长是短,“余生”的岁月是晴是雨,但他为不幸之后而万幸地拥有“余生”而暗自庆幸,从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便开始考虑如何快乐地度过这来之不易的余生。他在出狱后写的两首诗中表示:“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由此可见,苏轼的“余生”之念,并非始于黄州,而是在他出狱之后,还在赶赴黄州的途中,只不过是他在这首诗里用了“余年”的字眼罢了。四.黄州初期: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苏轼的“余生”是从黄州开始的。虽然已经走出了监狱,但苏轼并非是自由之身,他仍是受驱使、受管制、受监视的贬官,没有选择自己在何处度过“余生”的权利,“余生”的寄身之地与寄身时间都由朝廷安排,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苏轼的“余生”,自然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如自己所期待的那种“余年乐事”。初到黄州的苏轼,尚未没有完全摆脱乌台监狱的阴影,心有余悸。乌台乃御史台,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栖居其上,朝去暮来,齐声嘶鸣,令人惊恐。苏轼蹲的监狱是一口百尺深井,举手投足都会触碰到阴湿粗硬的井壁,他只能蜷曲身体坐于井底,只有井口上开着一个小小的天窗。他在这里关了一百三十多个日夜,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屈辱,以至“才隔一垣”的邻犯也感叹:“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眼前总会浮现那幽深的井,那凶恶的吏,那铺天盖地的群鸦……他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战栗,觉得这个世界突然有了太多的陷井,太多的险恶,太多的不测,他甚至自斟自饮的时候都不敢完全放松,唯恐喝得太多而酒后失言:“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定惠院寓居日夜偶出》)他到黄州后更不敢多写诗文,即使受人之求勉强作文题字亦反复叮嘱“乞不示人”,生怕别有用心者吹毛求疵,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再添新罪,令“余生”不得安宁。厄运使这位曾经笃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收养所)乞儿,眼见得天底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赤子,也有了防人之心。面对仕途断崖式的坠落,苏轼深陷于痛苦、悲哀与迷茫之中。苏轼亦政亦文,但他首先是政治人物,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想实现“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的抱负,曾被皇帝誉为可堪大用的宰相之才,常被重臣延为座上之位,自青年时代起即获显仕,列职儒馆,历典名城,主政地方,虽然其一直在五品知府的位置上辗转,但其为官为文的声誉令其拥有天下不敢小视的潜质和前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起步早,起点高,潜力大,后劲强。而经“乌台诗案”,苏轼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从五品知府直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职位低微且不得签署公文,无任何权力的小角色,成为一个被放逐被管制且漫无际涯的贬官,虽然还在体制之内,但其政治生命或许已经终结。这种打击对一直怀有仕途梦想与功业理想的苏轼几乎是毁灭性的。虽然他在《出狱诗次前韵二首其一》中表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似乎除了酒,余下都是身外之物,不必过于纠缠。虽然他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过“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的诗句,对自己作了一番苦笑式的自嘲。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失落和悲哀,对自己的“余生”一片迷茫,就像他来黄州路上遭遇的那场漫天大雪一样。苏轼纵然是一个天性乐观、胸襟豁达的人,但此时也难免心绪低落,他常常整天闭门不出,闷头大睡,从早到晚,睡得昏昏沉沉。他曾在给赵晦之的信里坦承:“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豖木石何异!”还有那种像江上浓不可化的雾团的孤寂感充塞在苏轼的心头。苏轼贬到黄州后,“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顿失社会联系,人际交往归零。尽管这种情况时间不算长,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一日不可没有朋友的性情之人,一个无时不需要人间温暖的孤寂旅人,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细腻且浓烈的热血诗人,其痛苦与沮丧是可以想象的。在举目无亲、出门无友的偏僻之地,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曾经在诗里叹息:“故人不复问通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如此之时,如此之地,如此之身,哪还有什么“余年乐事”,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伟大的灵魂也需要时间来疗伤。何况苏轼遭遇的是致命之伤。黄州之初,“余生”之始,苏轼的心还在滴血,伤口有待愈合,他无论是“故作达语”,还是暗自哀叹;无论是禅院听佛,还是探幽觅胜,都是在自舔伤口,反思人生,重新蓄养自尊自信,增强过好“余生”的勇气。五归去来兮归何处?东坡居士筑雪堂苏轼走入东坡,原本是他在黄州解决“余生”温饱问题之一举,却不意使他成为名传千秋的“东坡居士”。东坡不是名山峻岭,没有茂林积翠,没有云深雾漫,没有奇花异草,没有古寺名刹,没有先贤遗踪,没有任何的诗情画意,也没有任何的人文价值。它是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一块荒坡地,面积约有五十亩,曾经做过营地但废弃已久,荆棘丛生,瓦砾遍野,地力贫瘠,不宜耕种,如果不是苏轼的到来,它可能永远都处在沉睡与荒芜之中。苏轼来到这片坡地,实在出于无奈。他是一个“我生无田食破砚”的人,入仕以来一直靠领受俸禄为生,成为贬官后,官府只发给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来折算成薪水,他已无正常的俸禄可领了到黄州一年以后,苏轼有限的积蓄也几近耗光,一家老少的衣食之忧已无法避免。于是他的“余生”遇到了生存危机:“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幸好故人马正卿到黄州来看望苏轼,见其窘境,便自告奋勇地代苏轼去向黄州府申请拨一块荒地让其开垦,以助其维持生计。于是这片一向人迹罕至的荒坡地,终于被苏轼及家人、友人开垦、耕种的喧闹所唤醒;这片原来连个地名也没有的荒坡地,终于有了足与名山峻岭相媲美的名字:“东坡”;这片荒坡地的主人苏轼,也为自己起了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别号:“东坡居士”。在这片坡地,苏东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陇亩生涯。他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体力劳动者,从摇笔杆变成了扶犂耙,从庙堂走入了田亩,在这片荒芜之地辛勤劳作,孜孜不倦。他向农夫请教农技,仔细观看作物生长,改善坡地水土条件,忙得不亦乐乎虽苦虽累却充实无比。苏东坡总是戴上斗笠、穿着草屐、挽起裤腿、撸起袖子、扛着锄头出现在田垄地头,或乡间小路,或邻居屋前,与所有农人无异。这位“东坡居士”写了《东坡八首》以记录自己开荒、耕种的经历,他的诗含有汗水,带有泥土,夹有杂草,溢有稻香,是其田间劳作的再现,一切的场景与感受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和单纯,不见一丝之矫情,没有任何之夸张。这是他作为劳动者所写的田园诗,不像一些旁观者那样只把田园作为欣赏的一种风景和酒足饭饱之余抒情的对象,把田园生活写得那么悠闲自在甚至浪漫无比。尽管苏东坡如此辛勤劳作,然而他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里,其家庭的温饱状态仍然改善有限。我们从他的《寒食帖》里看见,“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空空如也的厨房里面只有冷冷的菜,破破烂烂的炉灶,烧的芦苇、木柴也是湿的。这种情形,说明苏东坡当时还没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那种感觉,他一家的温饱还是低水准和不稳定的。在这片坡地,苏东坡拥有了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初到黄州时,苏东坡与儿子苏迈寄居在定惠院里,后来全家到达黄州,临时借居在临皋亭里,一家老少二十多口住在里面,拥挤不堪。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着农闲动手在此建房,因房子是在大雪纷飞中建的,他美其名曰“东坡雪堂”,并以诗人的浪漫和想象,在四壁上绘上雪景,又自书“东坡雪堂”为匾。他是以扎根黄州、长住东坡的长远考虑来谋划建造“东坡雪堂”的,堂前屋后都栽有柳、红梅、松、桑、竹、桃等他喜欢的树。他对亲自设计和建造的“东坡雪堂”非常满意,烦有成就感,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给友人李公择的信中称:“有屋五间,果蔬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织,聊以卒岁。”拥有了这座足以为全家遮风避雨的住所,苏东坡的心情渐渐放平,开始随遇而安。他把“东坡雪堂”比作陶渊明的斜川,在其《江城子》词中,他为“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而欣欣然,为“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而痴痴然,为“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而坦坦然。在这片坡地,苏东坡加大了对黄州的感情投入。成为“东坡居士”之后,他不再闲门深居,不再闷头大睡,不再昼伏夜出,他主动地走出去,融入当地民众之中,与村夫野老、闾巷小民、乡间绅士?和尚道人成为朋友,其邻居庞大夫、郭药师、潘酒监、农夫古某更是他无话可不说的挚友。他经常与他们或闲聊、或共饮、或逗笑、或游乐,无拘无束,真诚相处,乐在其中。他在东坡围土筑塘时,村民们大力相助,令其非常感动:“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饿在我宁关天。”他还写过一首诗:“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他借此诗告诉远方的朋友: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我重返朝廷而费心了!正是与这些平民朋友的相处中,苏东坡得到了朝堂所没有的真诚与温暖,得到了切实的帮助与快乐,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安宁,所以当他受命离开黄州时,他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对自己的“东坡雪堂”恋恋不舍,他饱含深情地赋词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在这片坡地,苏东坡实现了脱胎换骨的人生涅槃。他在这里并没有止于心理调适,疗伤止痛,也没有止于适应环境,摆脱孤寂,而是在精神上有更高更自觉的追求他在自察与自省中进行了自我剖析,对自己喜欢“才华外露”、爱作书生空论等“取妍于人”的“多其病者”痛加批判,对自身的异己成份进行了无情的剥离;他在忧怨与激愤中走出了心理失衡,把乐天知命、委任自然演绎到极致,使自己能够真正做到宠辱不惊,安然自立走进了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和、宽广的精神空间;他在静坐与默修中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可以“一念清静,染污自落”,可以“表里翛然,无所附丽”,内心一片澄明、旷逸;他在落难与煎熬中炼就了一颗强大的心,可以笑看大江东去,可以迎接命运中更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轻蔑人生的一切磨难,可以实现对自己的、对时代的超越;他在不幸与痛苦中坚守了爱的情怀,他所承受的一切不幸与痛苦没有转化为恨与仇,而全部转化为爱的正能量,爱生命,爱人生,爱家人,爱亲友,爱民众,爱自然,用这这种深沉之爱、广博之爱去温暖自己,温暖别人,温暖人世。在这里,他对自己身上长期摄收的儒道佛三家进行了圆融与贯通,也有过滤与扬弃:他汲取了儒家之说以坚守入世的精神,心系社稷,而又不令自己变成功利之徒;他汲取了释道之学以免内心的崩溃,达观自适,而又不把自己变成孤寂之人;他汲取了佛家之道以实现自己的解脱,超然物外,而又不使自己变成遁世之士。正如苏东坡在《答李端叔书》中所言:“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而不是今天的我。即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轼是两个人。在黄州,在东坡,那个竹笠草履,面黑如墨,带月荷锄而归的苏东坡,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苏轼,他是阅尽人生沧桑后更加旷达和洒脱的君子与智者,他是历尽了疾风暴雨之后更显倔强和风姿的劲草与修竹。六.三咏赤壁:如无苏仙前后赋,岂得佳名天下布苏轼在黄州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不仅别人没有想到,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没有想到接纳他的黄州山水,荒芜东坡,令他由苏轼变成了苏东坡,由昨天的他变成了今天的他,一个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他。他没有想到自己不仅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得以升华,而且他作为因诗获罪的诗人竟然变成了超越自己、穿越时空的伟大词圣。不仅仅是词。因为那场牢狱之灾,因为这次谪罪之居,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太多,其内心世界累积了太多的生命体验需要书写,拥有了太多的人生情怀需要释放,储存了太多的审美光能需要喷射,于是他的创作如火山爆发,似江河决堤,气象万千,绚烂多姿,奇迹般地使其文学和艺术创作进入了黄金期。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傲视千秋,永放光芒,绘画也独树一帜,为文人画的开山而影响深远。他三咏赤壁的一词两赋更是震古烁今,以其铁板铜琶的雄壮与悲凉而成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里,有大江东去的气势,风流人物的气慨,历史烟云的聚散,千秋功业的兴衰;也有英雄美女的故事,早生华发的惊愕,人间如梦的感叹,江水明月的永恒。在惊心动魄的壮阔、淋漓尽致的豪放、无与伦比的超旷之中,寓着深沉的“悲慨”和深情的眷恋与向往。作为苏东坡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横空出世,为当时多为靡靡之音的北宋词坛辟出了豪放词风的崭新天空。词的题材由此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儿女情长、离愁别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的各和意绪与情怀皆可入词成韵。词风也不再只有婉约缠绵、绮丽柔靡,可以有恢宏气势、雄浑意境和豪放襟怀。苏东坡从怀古感旧出发,将词这一诗歌形式提升为表达胸襟抱负的黄钟大吕,于是“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在《赤壁赋》里,苏东坡引领我们进入秋夜长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意境之中,再让我们聆听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箫声,然后才进入主客的思辨性对话。面对客之洞箫把饮酒欢歌的场面吹成满耳悲戚,面对客为曹操这样的“一世之雄”也化为过眼烟云的慨叹,面对客为人生短暂而长江之水却无穷无尽的哀鸣,面对客只能把深深的伤感“托遗响于悲风”的无夸,苏东坡以水月为喻,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阐述“变与不变”的深刻见解:“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偿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共食。”思辨结束后,主客醉酒而眠,心灵与天地之美融为一体。在《后赤壁赋》里,已不是主客对话,亦无思辨色彩,叙述的是苏东坡在明月下独自爬上断岸的一次冒险经历。这是登高俯视长江的视角,与前《赤壁赋》里泛舟江流不一样,但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令其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面对夜里深不可测的江水,苏东坡“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又见“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诗人的“划然长啸”与孤鹤的“戛然长鸣”有何隐喻?诗人对道士亦鹤、鹤亦道士的描述又有何用意?他都没有点破,而使之显得迷离恍惚,玄妙莫测。也许我们唯有走进苏东坡的心路历程,方能领悟到其中的含义和与前《赤壁赋》的内在联系,读懂此传世佳作。这两篇赤壁之赋,写的季节不同,前赋为“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秋日,后赋为“霜露已降,木叶尽脱”的冬天;叙述的方式不同,前赋谈玄论、亦思亦辨,后赋叙事描景、亦实亦幻;呈现的风格不同,前赋是清爽之气、旷达之怀,后赋是寥落之氛、幽峭之意。然而都是高妙之笔,其意义在于“让中国文章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这是苏东坡对有山水韵而缺乏水墨味的汉赋的重大突破,对有水墨味而缺山水韵的六朝文章的卓然超越,成为苏文的巅峰之作。正如施扆宾所言:“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迤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史言共为珍宝。”这是苏东坡对中国文章的重大贡献。再看看苏东坡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赏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头已白。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苞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此诗意味苦涩,苍凉惆怅,似与苏东坡谪居黄州进入第三年后已渐渐抚平痛苦与忧伤的情形有异。也许是某一个动念间,他又被压在心底某个角落的哀愁触碰到,而悲情重起,而幽咽难抑,深深回味,却又不失旷逸与苍劲。这首诗在苏东坡的众多诗词中并非最杰出,然而作为书法作品,其奔涌而出、淋漓尽致的情怀,恣肆奇崛、浑然天成的结字,起伏跌宕、且疾且稳的布局,看似随意、实则耐品的字型,使诗心与书法意蕴融为一体,而成为伟大名作。《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被尊为“天下三大行书”之一,其一气呵成,犹杂神助,黄庭坚说“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即假如苏东坡重新来写,也未必能写得这么好。作为苏东坡的书法代表作,此帖的横空出世,意义非凡,如学者所说“实现了书法功能的又一次超越。这种超越,虽有书法规则确立的基础,但绝不是简单的变革。它需要时代的酝酿,也需要个性、禀赋、学力的滋养,更需要苏东坡其人品性依托和开发。”苏东坡这些千古不朽的词、赋和书法无一不是诞生在黄州,在东坡,在“雪堂”。谁都没有想到,这段谪罪之旅,这个偏僻之州,这片荒芜之地,这座简陋之所,竟成为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殿堂。寓黄四年余,不仅成为苏东坡创作生涯的井喷时期,而且使他登上了创作成就最高最辉煌的巅峰。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这黄州,这东坡,与苏轼都在互相等待,互相拥抱,互相成全,即这块土地成全了苏轼,遂诞生了自号苏东坡的人,一个可以独立于苏轼的伟大存在,一个即使截去苏轼之前的一切也毫不影响其价值的光辉人物,而东坡也成全了这片土地,成为黄州的文化符号,成为赤壁的魅力所在。此赤壁原本只是传说而非实地的三国古战场,全赖苏东坡的“三咏之功”而名扬天下。南宋诗人王炎有感于黄州赤壁的奇迹而赋诗一首:“乌林赤壁事已陈,黄州赤壁天下闻。东坡居士妙言语,赋到此翁无古人。”黄州赤壁的故事和美名甚至传至海外,苏东坡辞世六百年后,朝鲜诗人尹善道感叹道:“赤壁自古争战地,风流偶与苏仙遇。如无苏仙前后赋,岂得佳名天下布。”因为仰慕苏东坡,朝鲜时代的诗人还将江边上的一处绝壁想象为苏东坡笔下的赤壁,并效仿其泛舟其间,赏月览景,久而久之,竟成风气。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总结自己人生所写的诗句。这不应视为他的自我解嘲,而是他发自肺腑的自我评价。回望山重水复的来路,追忆风风雨雨的岁月,苏东坡完全了解自己平生最大的功业不在仕途,不在意气风发之时,不在玉堂金马之时,不在位高权重之时,而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处落难之地,贬谪之地。而黄州是苏东坡的首贬之地,更是他的重生之地,他在这里实现了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成就了伟大的灵魂,开始了智慧人生,他更在这里写出了千古绝唱。他在谪居黄州四年零三个月,创作的词赋名篇远非其他时期可比,展现了其天才的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黄州堪称是苏东坡人生最有价值的第一州,而黄州东坡则是他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历史已经记住,未来仍将记住:苏东坡是在黄州的“余生”走向光辉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