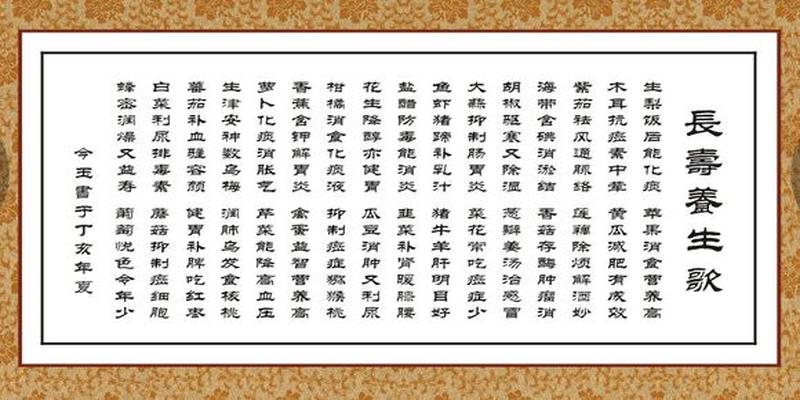东兰坐在酒席上吃着盘中的美食,看着新郎新娘在一大帮人簇拥下给旁边桌子上的宾客敬酒。村上稍微家境好一点的人家都娶上媳妇了,家里两个儿子也不小了,大的九二年的,小的九三年的,也应该娶媳妇了。唉!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像这邻居家的孩子一样热热闹闹地把婚结了。
东兰今年五十出头了,三十六岁那年老公脑溢血突然就走了,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年迈的公婆。老公是独生子,公婆把东兰当作了依靠。那时有人来说媒,都给公婆挡了,她走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东兰也麻木了,像一头老黄牛一样,拉着这个家晃悠着向前。
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孩子要上学,东兰去了江苏无锡打工,钱一分都舍不得花,衣服都是工作服,沒烫过头发。说话做事也是越来越干脆利落,性子越来越倔犟,一个女人终究活成了女汉子。
前几年,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年迈的公婆帮衬着她一起盖了两间新楼房。然后是婆婆走了,去年公公也走了,她披麻戴孝给老人料理了后事,从此再也没有人会拦着她嫁人。
东兰照着镜子,镜中的人憔悴、苍白,脸上没有光泽,眼角有了皱纹,头发剪得短短的,过半百了,两鬓有几根白发了。眼睛里看不到清澈明亮,有点无神无助。这个样子,还有男人喜欢吗?还有值得嫁的男人吗?她胡思乱想着,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这一辈子命怎么这么苦?是生下来就安排好了的么?东兰无处诉苦,无人可诉。
儿子也不小了,都是适婚年纪了,这农村的新房还能让他们娶到老婆吗?彩礼钱还没存上,儿子们也不是那样会来事的人,苦日子里泡大的孩子多少有一点不自信,没底气。唉,真难。
又降温了,坐在小凳子上的东兰,手捧着脸,眼睛看着远处雨雾中隐约的山峦,个子小小的她踡缩着身子,不胜寒冷。
接亲的队伍已经到家门口了,儿子抱着新媳妇进门了,她想找一件漂亮点的鲜艳一点的带红色的外套,可是翻遍了柜子也没找到,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墨绿色工作服,她急得一头汗。坐着竟也能睡着,不过这样的梦多少能给她带来一点欣慰,她嘟了嘟嘴。
(文中的东兰是厂里的一位女工,她说她要请一天假回去喝村上邻居的喜酒,只因她对我说:她的命怎么这么苦。有了想写一写她的欲望。一直沒嫁的她用一生坚守着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