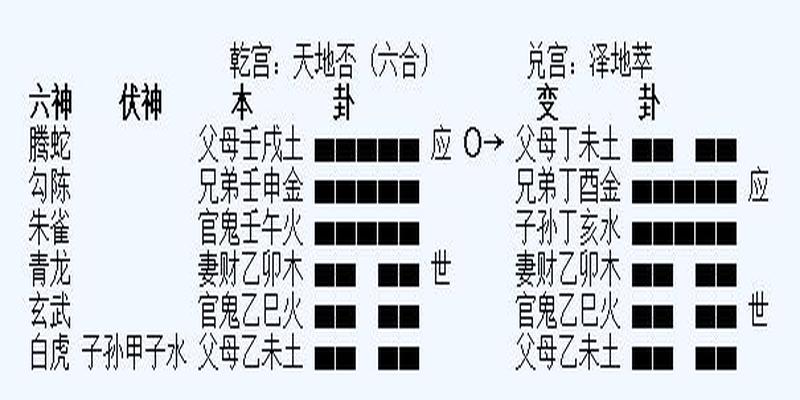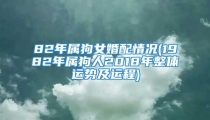连翘有过一个美满的家,丈夫疼爱,婆婆顾惜,一家人的日子虽说清苦,倒也其乐融融,然而这一切在连翘九死一生的生下女儿小萝卜后便日渐稀疏,只因为接生婆婆的一句话,“这丫头,生的倒好,只是这眼下的一颗黑点点,像是个落泪痣,怕是……”“落泪痣?!怎么会……”婆婆一边一叠声的说着,一边伸出手来在新生儿薄嫩的皮肤上用力的揉搓,似乎这样就可以揉搓掉她心里莫名的慌乱和嫌弃。“其实也没啥,那都是老辈人的讲究,你看这孩子哭声震天介响,白白胖胖的多招人疼……”接生婆婆心恨自己多嘴,生怕主家心有不快薄待了她的荷包,不得不又打起圆场来。“落泪痣,在家克父,出嫁克夫,怎么招人疼!长在哪里不好,偏生长在眼角下……”婆婆看着昏沉睡去的连翘,抱起哇哇大哭的小小婴儿,长叹一声,轻轻摇晃,喃喃低语,一滴浊泪悄悄落下,“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接生婆婆再不敢言语,拿了谢礼逃也似的快步离去。连翘刚出了月子便听到了镇上的风言风语,婆婆对她们母女的冷淡和疏离她不是不知道,但她一直以为是因为嫌弃她生的不是个传宗接代的男娃,她还打算着等女儿小萝卜稍大点再给她添个弟弟……原来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因为小萝卜脸上的一个小小的黑痣。“娘,您心里要是不舒服,等小萝卜大一点了,我带她去医院给点了去就行了,就是一颗小小的痣嘛……”连翘一边笑嘻嘻的哄着婆婆,一边打量她的脸色,见婆婆不语,把怀里抱着的白嫩的小萝卜一下递到婆婆面前,“你看,她长的多好!”“才多大,就能看出长的好赖!”婆婆瞟了一眼正酣睡的白白嫩嫩的小女娃,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抱在了怀里。尽管心里有个疙瘩,但血脉相连,终究还是心疼,或许这泪痣也只是一颗寻常普通的黑痣而已。时间过得飞快,门口的合欢花树花开了五回又落了五遍。肉乎乎的小萝卜抱着一只同样肉乎乎的黄白花的小狗,蹦蹦跳跳的跟在连翘身后,头上别着一朵粉嘟嘟毛茸茸的合欢花,正咿咿呀呀的唱着儿歌,“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娘,毛驴我不骑,留给弟弟骑!”连翘抚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噗嗤”一声笑出声音,“你怎么就知道是弟弟?不是妹妹呢?”“我已经有花卷当我妹妹了,它不会跟我抢爹给我买的花裙子!”花卷是小萝卜给小花狗起的名字,因为她尤其爱吃娘亲手包的萝卜豆腐馅的花卷。小萝卜此刻嘟着嘴,扭着身子,长长的睫毛垂下,眼角下的小黑痣衬得一张圆圆的小脸生动且可爱。“你爹进城卖鱼也该回来了,怎么今儿这么晚?”连翘站在门口伸长了脖子朝着路口张望。“爹还说今天要给我买花裙子回来呢!”小萝卜学着连翘的样子探着身子看向远方,高兴的笑着,拖起的尾音带着一点点俏皮的上扬。“可不嘛,今儿可是咱小萝卜的五岁生日嘞!”连翘轻轻的拍了下小萝卜毛茸茸的小脑袋,花卷窝在小萝卜的手臂上睡得正香。一只黑色的老鸹鸟扑棱着翅膀掠过夕阳下斑驳的光影,发出“呱呱”的聒噪声,让人无端的生出心慌烦闷来。“呸呸!别处叫去!”婆婆一手拿着树枝驱赶着鸟儿,一手拎着一包糖果,蹒跚而来。“小萝卜今儿过生日,我称了一包酥糖给娃儿吃,这也五岁了,翻过了年儿,让她爹带她去医院把那痣点了吧,人长痣大,不好。”婆婆这些年也不是催过连翘一回两回了,连翘总心疼孩子还小,一拖再拖。“行,娘,翻过了年让她爹带她去医院看看去。”“连翘,大娘,快去看看吧,萝卜她爹出事了!”村长一脸惊惶的汗水,看的连翘的心“突突”的跳着往下沉。小萝卜爹回村的时候,拉鱼车的驴受了惊,车翻到了路边的旱沟里,萝卜爹也只剩下了半条命,躺在县医院里昏迷不醒。连翘拖着小萝卜赶到的时候,只见他的手里还紧紧抓着一条满是灰土沾着零星血迹的粉色碎花小连衣裙,那是小萝卜的生日礼物。“爹,你起来,你快起来,别睡了!我不要连衣裙了!爹……”小萝卜哭的栖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颗颗滚落。“哭!哭什么哭,你爹又没死!你嚎什么丧!”婆婆的眼睛红肿,头发蓬乱,盯着小萝卜连声的吼着,“都是你!生了个落泪痣,简直就是丧门星!这下好了,果然应了克,你爹断了一条腿,这都是你克的!”小萝卜瞪大了惊恐的眼睛,抽抽噎噎的躲在连翘的身后,紧紧的拉着连翘的衣襟。“娘!她还小,你别这样说她,毕竟是你孙女,天灾人祸怎么能怪到萝卜身上?”“都是你,不争气,生个丫头片子还不祥!”婆婆完全变了一个人,尖酸刻薄,咄咄逼人,状若疯癫。也或许这些就是她长久以来埋在心底里的话,终于奔涌着找到了一个出口。连翘紧紧搂着小小的小萝卜,红着眼睛轻声安慰,“别怕,乖乖,别怕!”这一场事故简直让这家人的日子急转直下,连翘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想着哪家的亲戚朋友那里还能借出来一点钱,婆婆每天除了在病床前守着自己的儿子,其余的一概不管,偶尔看向小萝卜的目光总是充满着厌恶和嫌弃,所以连翘无论去哪里都把小萝卜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奔波劳累,让连翘动了胎气,最终没能保住肚子里那个弱小的生命,婆婆在听医生说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的时候,一个倒仰,背过气去。小萝卜偎依着连翘躺在病床上,像娘哄她睡觉一样,一只肉乎乎的小手轻轻的拍着连翘的胳膊,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刚刚五岁的孩子在这一系列的变故里已经学会了无声的落泪,小小的身体里不知道装着多少的害怕和惊恐。昏睡的连翘睁开眼的时候习惯性的往身侧摸了摸,软软的小人儿不在身边。连翘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拖着虚弱的身子下床呼唤着小萝卜。病房没有。走廊没有。好心的护士告诉连翘,婆婆带着小萝卜出去买吃的去了。连翘心下稍安,到底是亲生的孙女,好歹还是心疼的吧。正想着,婆婆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娘,小萝卜呢?”连翘歪着头朝着婆婆身后看去,空无一人。“没看到,不是和你一个床上睡着吗?”婆婆的目光有些闪躲,眼圈青黑红肿,整个人再没有原来的慈祥和蔼。“娘,护士说是你带她买吃的去了,不是你带的吗?”连翘的声音因为焦急害怕而尖利起来。“我没带,没看到!”“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连翘哭喊着拉扯着婆婆,一个牛皮纸信封从婆婆怀里掉了下来,信封口隐隐露出一叠纸币。连翘呆了一下,婆婆趁机捡起信封夺路而走。吵闹声招来了院内安保,等到公安来到医院找到婆婆的时候,她正躲在医院的茶水间里哭的鼻涕眼泪横流,嘴角挂着血丝,面上红肿,看着似乎是层层叠叠的巴掌印。婆婆不承认故意丢弃了孙女,只说是不小心丢了小萝卜,遍寻不到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媳妇交代所以才撒了谎,至于那些钱,是她多年积攒下的棺材本,要给儿子交住院费的。公安派人立刻查找,登报纸寻人,电视电台滚动播报,可小萝卜踪迹全无,毫无消息。连翘简直疯了一样,拖着病弱的身体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一遍遍的呼唤着小萝卜的名字,短短的几天下去,人已经瘦的不成样子,似乎一阵风来就可以吹着她去了。公安已经因为她出了多次警,她总是认错人,看着四五岁的小姑娘她都要拉过来看看是不是她的小萝卜,每每被人骂做疯子。小萝卜爹在躺了半个月后悠悠醒来,得知一切后,偷跑出医院,拄着拐杖,拖着残躯到处去寻他心爱的女儿。终于在一个落雨的午夜倒在了路边,再也没有醒来,怀里还揣着那件粉色碎花的小连衣裙。婆婆一夜之间白了头发,苍老脆弱的像是一片枯败的落叶,每天躺在床上再不愿出门,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话,“报应……”一时之间的恶念通常都来自心底里长久以来的恶意,婆婆故去的时候,连翘一滴泪都没流,尽管婆婆不曾承认,可她明了一切,但她不知道的是怎样才能找回她心心念念的女儿。往日温馨热闹的家,最终只剩了连翘一人,陪着她的只有日渐老迈的花卷。十多年过去了,门口的合欢花树愈加茂密,每到花开的时节,连翘总坐在门口呆呆的一看就是一整天。撤县设市后,医院和公安局的人员调动更替,但他们都认识连翘,都知道连翘丢了个女儿,她叫小萝卜。秋夜的雨总是细密而绵长。连翘抱着小萝卜曾经枕过的已经褪了色的碎花小枕头,在夜半的梦里似乎又把曾经的那些日月放电影般又过了一遍,醒来时照旧是泪流满面。花卷急切的吠声在雨夜里回荡,它近两年老的厉害,耳朵聋了,眼睛里也长了白翌,通常是一夜睡到天亮,像这样的夜吠已经好久没有过了。连翘抹了把脸,回了回神,披件衣服下床。花卷看到主人出来,起劲的摇着尾巴,吠声更大,身边一个小小的提篮里发出微弱的哭声,在“沙沙”的秋雨中和犬吠里几不可闻。连翘急忙提过篮子进屋,花卷抖了抖身上的雨水,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嘴里发出小孩子一样的“哼唧”声。灯光下,一个瘦瘦小小的孩子躺在篮子里,大红色的披风已经被雨水浸潮,稀稀拉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小脸上满是雨水,一个信封放在孩子身下,写着一串数字,应该是这孩子的出生日期。“造孽啊!这是哪家心黑的,嫌弃是个女娃吗?”连翘擦了擦孩子脸上的水,一边絮絮叨叨的翻找出小萝卜小时候的小衣裳给孩子换上,经常的晾晒清洗让这些小衣服拿出来的时候还带着肥皂清爽的气味。花卷一直守在旁边,轻轻摇着毛发稀疏的尾巴,一双混浊的老眼看着那孩子竟像是透着慈祥和欢欣。天一放亮,连翘就带着小女娃去了趟新街,拿出皱皱巴巴的钱来买了一袋奶粉和一个奶瓶。温暖的晨光里,孩子用力吮吸的样子,让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小萝卜,十多年过去了,小萝卜也该长成个大姑娘了,或许某天与她擦肩而过,也是互不相识吧。村长是在第二天的傍晚来到连翘家的,他蹲在门口吧嗒着旱烟,看着连翘怀里酣睡的孩子,老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这孩子,你打算养着?好歹也要去找公安说说情况。”连翘这些年的煎熬他们都看在眼里,村长也不是铁石心肠,但总归村长自有村长的觉悟。“行,去说说吧。要是没人找我想先养着,要是她爹妈来找,我就,我就再还给人家。”出乎村长的意料,连翘虽然不舍,但答应的很是爽快,村长一下觉得心里松了一口气。“那行!我和你一道去着,你等着,我让我家大喜开着队里的柴油机送我们去。”公安局上上下下没有不认识连翘的,简单做个笔录,就让连翘暂时带着孩子回了家,村长送来了米面和油,大喜把自家孩子穿小的衣服鞋子送来了一堆,大喜媳妇说,她奶水多,可以给这可怜的孩子喂喂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公安没有传来有人报警寻人的消息,连翘也再没去公安局和市医院转悠过。小小的奶娃娃一天天的长开了来,或许是错觉,连翘总觉得这孩子眉眼之间似乎有小萝卜的影子,肉肉圆圆的小脸,长长的睫毛,除了脸蛋上没有泪痣。连翘给孩子起了个名字,缨子。她似乎从十多年的噩梦里醒了过来,脸上渐渐又有了笑容,缨子第一次咿呀学语叫她“婆”的时候,她笑得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的像是天边红红的彩霞。老狗花卷时刻偎依在缨子的旁边,尽管它已经老的瘦弱不堪,但一旦有生人靠近缨子的时候,它仍然会气势十足的露出犬牙,呜呜吠叫。这天一早,连翘家里来了个稀罕客,白发苍苍的接生婆婆拄着拐棍,吃力的拎着一袋东西进了连翘的家门。“您老来就来,还带啥东西?”连翘有点摸不着头脑,自从接生过小萝卜,她与接生婆婆再无交集。“给缨子买了两件衣服,也不知道能不能穿,我瞧着这孩子你带的甚好,这长的白白嫩嫩的,可比刚来的时候鲜亮的多了!”“您不是去了省城的闺女那养老了吗?这回来在家待不了几天吧?”连翘有些疑惑,听着接生婆婆的意思,好像她老早就见过缨子一样。“落叶总要归根的,闺女那个妇产科医生的工作,白天黑夜的忙,我在那里也是无趣的很,还是回来好,老话说的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接生婆婆沉默片刻,看了看可爱的缨子,接着说道,“连翘,我今儿来,有话对你说,”她艰难的咽了咽唾沫,“其实当年都怪我,怪我多嘴,说了小萝卜那是落泪痣,引得你婆婆种下了心结,这些年,我越想越觉着对你不住,也对不住小萝卜……”连翘看着面前满头白发的老人,眼圈肿胀,喉头酸涩。这猝不及防的歉意,让那些旧事毫无预兆的涌上心头。连翘长长的叹息一声,沉默片刻,“算了,都过去了,这也不能怪您。您年纪大了,心该宽一点。”“现在你有了缨子,好歹也有了盼头,有啥我这个老婆子能帮上的,也让我尽尽心,让我好过点。我这辈子没做过别的亏心事,只多的这句嘴让我觉得对你不住。”千叮万嘱后,接生婆婆拄着拐棍蹒跚而去。门口的合欢花开的正艳,远远望去似一片粉色的烟霞,一阵风过,朵朵小花打着旋儿的落在地上,连翘捡起一朵,轻轻别在缨子的耳朵上,小小的娃娃便咯咯的笑了起来。天气越发热了起来,缨子的身上起了不少的痱子,大喜媳妇给缨子送来痱子粉的时候悄悄的跟连翘漏了口风,听说有人看上了栖霞河,想在这里建个湿地公园,老街在规划范围内,估计要全部拆迁,以新换旧,这处老房子,连翘和缨子怕是住不了几天了。连翘的一颗心登时像是在滚水里上下煎熬,小萝卜还没回来,她说什么也要等在这里。事情进展的很快,栖霞镇上一些陌生的面孔多了起来,见天儿的在栖霞河边转悠,转悠的那油光锃亮的皮鞋上沾满了泥巴坨坨。无论村长说了多少好话讲了多少大道理,连翘就是梗着脖子不搬,一辈子老实巴交的连翘,老了老了,倒当起了“钉子户”来。一场雨后,天气难得的凉爽,门口的合欢花在雨里落了一地,不知哪里飞来的一只喜鹊,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叫的甚是欢快。天气忽冷忽热,让缨子这两天有点感冒的症状,连翘甚是焦心。“连翘,在家不?”村长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啥事?要是搬迁的事就别说了,我这赶着要出门。”连翘一边应着村长,一边抱着缨子拉开了院门。一个身穿碎花裙的背影立在那棵合欢花树下,出神的看着落了一地的粉色小花。花卷依偎着蹲在一边,不时的伸出鼻子来嗅着身边那人垂在身侧的手,嘴巴里发出了孩子一样的“哼唧”声。连翘有一瞬的恍惚,似乎看到了一样穿着粉色碎花裙的小萝卜。“哇!”的一声大哭打破了寂静,缨子闹将起来。“村长,你看,缨子病了,我赶着去医院,有事等我回来说吧。”连翘手忙脚乱的把院门落了锁,急急忙忙的就往前走。“孩子病了吗?我送你去吧,我开着车,很方便的。”一道清亮的女声在背后响起。“那敢情好,就麻烦齐总了。”连翘刚想回绝,身边的村长已经替她应了下来,还不住的朝她递着眼色,一副不用白不用的狡诈表情。“不用那么客气,叫我齐杨就行了。”边说着话,边跑了过去拉开了车门。“那多谢了。”连翘坐了上去,软软的坐垫,果然和班车不一样。“没事,别客气。”齐杨关了车门,转头对着连翘一笑,眼角下面一个圆圆的小黑痣清晰的映入了连翘的眼帘。连翘瞬间僵在那里,一堆杂乱的念头疯了一样涌入心头。(小说名:落泪痣,作者:茉茉的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