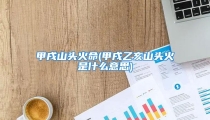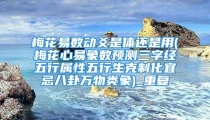《东坡志林》洋洋洒洒数百篇文章,所载的多为作者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所写的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而此间苏轼正经历仕途的一贬,再贬乃至第三次被贬。作品淋漓酣畅地记载了东坡的谈天说地,出游交友,入仕致仕,他的洒脱豪放之性情一览无余。通读五卷本的《东坡志林》我们会从中发现有三篇短小文章集中地谈到“命运”,即卷一中的《命分》三篇。名称分别为《退之平生多得谤誉》、《马梦得同岁》、《人生有定分》。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三篇不足二百字的短文(含标题182字),却让人体会到苏轼曾经不幸的心理遭遇和无助的精神折磨。如对三篇文章的创作时间忽略不谈,那么三篇短文恰能隐约表现出苏轼那个特殊的阶段时间内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自我安慰、稍存希望到回归现实、接受挑战最终向命运低下了的头。也可以简单地描述成:希望、失望、绝望的变化过程。前朝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应为苏轼所敬仰,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给予韩愈以很高的评价,其中“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更为世代所传诵。苏轼了解韩愈的一生,韩愈的一生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人生。元丰三年(1080年)的大年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从京城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二月初一到达了黄州——长江边上一座偏僻的小镇。由于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苏轼的人生一下子跌到最低谷。余秋雨先生的《东坡突围》中有更精彩的描写: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苏轼当然不会忘记韩愈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时的苏轼,心意之冷、心情之差,心绪之乱丝毫不会低于那时的韩愈,因为苏轼想到了韩愈,想到了自己和韩愈相同的命运。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退之平生多得谤誉》苏轼不仅想到韩愈而且找到了和韩愈命运的相同点,即命宫同为“磨蝎”。面对浩瀚的星空,寂寞孤独的苏轼定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韩愈的人生经历进行置换,最终结果不会否定韩愈,也不会怀疑自己。想到了韩愈的平生遭遇(韩愈一生屡谏屡贬,屡贬屡谏),作为相同类型的苏轼,也就产生一丝丝的内心平静。如文章所说“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用今天的话说:这一生会受到很多的诽谤和赞誉,估计和韩愈差不多。尤其是“殆”字的使用,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此时的苏轼应该对命运的奇迹充满着希望,他在期待着。从他此时创作的名篇《卜算子》中也能读出些许意思:虽然“飘渺孤鸿影”但依然“拣尽寒枝不肯栖”。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再看第二篇,此篇同样也写到了一个人,马梦得。毫无疑问,此人肯定不是什么文学大家或皇亲国戚,也不会是往日的汴梁城中苏轼家里高朋满座中的一员。但是此人心地善良、且与苏轼甚为友好。据说,在苏轼被贬不久后马梦得也追随他来到了黄州,而且向黄州太守请求“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期间马梦得不仅没有在意苏轼“犯官”身份而且与苏轼交往频繁,他带给苏轼情感和心理上的安慰之大可想而知。当然,从“居庙堂之高”到“退江湖之远”的巨大变化所带给苏轼的内心打击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因为有了好友的帮助,再加上全家人不久都到了黄州,这还是给了他一些精神慰藉,苏轼接受了生活现实,现实的生活也摆在了苏轼的面前:生活愈加艰难了。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地位的变化自然会带来交往圈子的变化,圈中的朋友身份配置和选择也就发生了变化。无论为了自保还是为了避嫌,相信此时苏轼的身边已经没有昔日的好友了,过往的喧嚣和所谓的热闹早已“灰飞烟灭”。无疑,马梦得成了苏轼生命这个阶段中最重要一个人了。所以,苏轼的感受往往来自于眼前这位位低权轻的朋友。巧合的是马梦得与苏轼同年同月出生,只是比苏轼小八天,苏轼很快就从这个朋友身上找到了共同点。当然这个共同点不是来自于人生经历而仅仅是一串数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苏轼是如何得出“是岁生者,无富贵人”的结论的,或者仅限于两个人的生活境遇的判断。但是他坚信在所有同年生的“无富贵”之人中,他和马梦得应该排在最前面。聊以自慰的是,梦得还得排在他的前面,也就是说梦得比他还穷、还不幸。从选择的对象和比较的内容上看,此时苏轼已经降低了对人生的期许和目标。从“磨蝎”命宫的“平生多得谤誉”到“是岁生者,无富贵人”的冰冷数字的关注,苏轼对人生和前途的思考越来越内向,思维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失望之情可见。再看第三篇,此篇已经无人可写了,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空间内已经没有谁和他有相同的境遇了或能带给他命运的共鸣了。生活的折磨和岁月的流逝已经让苏轼彻底地放低了自己曾经深邃的目光和收敛那一缕向上的心绪。他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坛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这段文字同样来自《东坡突围》。隐约间我们感受到了苏轼向生活或者说命运祈求的无奈:“吾无求于世,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作者此时的最大追求已经降至了“温饱”问题,即“粥”了。粥,稀饭,此时的粮食奇缺可见一斑,生存状况的恶劣可想而知。最终作者发出了“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的“天问”即:老天爷,难道我的命运如此的艰难,就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吗?作者目光和视野所及仅限于命运了——“人生自由定分”,而这“定分”也绝不是功名富贵的追求而是温饱之事了。此时一切都是为了“活命”。为了保命的“粥”,苏轼终于向“命运”深深地弯下了腰。饥饿让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彻底失去了“尊严”。想当年苏轼父子名动京城,尤其是欧阳修曾盛赞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的发展也如欧阳修的称赞那样:声名大噪,每有新作,会立刻传遍京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那时苏轼是何等的自信,又是何等的风光。此时,为一“粥”而哀天悯地的苏轼,他的内心世界的痛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用“绝望”一词概括实不为过。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他指出,低级需要直接关系个体的生存,也叫缺失需要,当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直接危及生命;高级需要不是维持个体生存所必须的,但是满足这种需要使人健康、长寿、精力旺盛,所以叫做生长需要。比较一下苏轼的三篇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需求变化,对于一个名震京师的大学者而言,明显是成倒金字塔型的从高到低的追求:从内心的交流对象上看,从“韩愈”到“马梦得”最后变成了一碗“粥”;从精神空间的寄存物上看,从万人尊崇的“文学家”到一介“书生”最后沦为毫无生命的“粥”。苏轼的生命质量追求终于从最高的“生长需要”沦为“缺失需要”。这不是苏轼的悲剧,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同样被记入《东坡志林》的《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如果彼时苏轼还有闲情于对月感慨,那么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闲人”了而是食不果腹的村野匹夫了,应该是大宋王朝最底层的那个人了。改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苏东坡在挨饿,整个民族在丢人。这就是苏东坡的命运。附:《命分》三篇。退之平生多得谤誉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马梦得同岁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人生有定分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