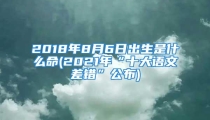人到晚年总有想要抓住点什么的奋力感。但面对彼此,老人们普遍不知道聊天怎么开头,自由恋爱要怎么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好感?怎么打动对方的心?这些问题很难,但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对孤独的老人们来说,许多事比相亲更重要。文|易方兴编辑|楚明对以“老人相亲圣地”闻名于北京的菖蒲河公园来说,来这里的老人们可能都知道,菖蒲河是一个打“争上游”的好地方,是一个发掘陌生舞伴的好地方,也是一个感受热闹的好地方,唯独不是一个相亲的好地方。几天前,几个衣着鲜艳的外地离异中年女人为这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公园里有的老人跃跃欲试;有的直摇头:“又多了几个骗子。”“骗婚”的故事在菖蒲河公园里流传。故事有许多版本,比较通用的版本是,一个外地离异中年女人为了得到北京户口和房产,在公园找了个比自己大30岁的单身老人结婚。结婚几年后,老人就去世了。也有在公园相亲成功的。“百分之一。”78岁的张秀芬说。她来菖蒲河已经1年,每周二、六日,风雨无阻。她想寻找真爱。什么是真爱?“就是愿意听我说话,日子也能过到一起去,不用凑合。”张秀芬经历过两次“凑合”婚姻。第一段婚姻,她没能生出儿子,丈夫不要她了;第二段,丈夫在厂里做工,身体不好,她照顾了他16年。到2012年,第二任丈夫去世了。她说自己“不能甘心”,但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菖蒲河公园位于天安门东侧,开放于2002年9月,成为老人的相亲圣地还是在这几年。长安街旁边的老红墙把窄小的公园和120米的宽阔马路隔开,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车水马龙,另一个世界里语速、行动、时间,什么都慢。毋庸置疑的是,如今的菖蒲河公园,是老人的天下。如今的菖蒲河公园是老人的天下。图/网络远远地在长安街上,就能望见菖蒲河公园亭子里密集的老人。如果用60岁来划分,老年人的数量在中国已有2.4亿,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亿。空气从冷的地方流到热的地方,就形成了风。人老了之后,会希望从冷清的地方聚集到热闹的地方,就形成了如今菖蒲河公园的景象。去年冬天,一个身穿军装的80岁老人慕名来到菖蒲河公园。他不苟言笑,腰板挺得笔直,用5分钟从公园亭子的这一头走到百米开外的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回来。老人们给他取外号叫“大校”,议论他的退休收入,“怕是一个月有1万多”。好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上前搭话,发现“大校”要求太高,要找年轻和收入高的,于是又退了回来。而年轻的则被那一身军装吓退了。到了今年冬天,大校已经81岁,依然穿着军装,从亭子一头缓慢地走到另一头。大部分老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有一个住在通州的60岁男士,每周六雷打不动地从通州坐647路再倒1路车来到这里,路上来回4个小时。但他觉得很有必要,说周六在公园里找他搭话的人,比他一整周其他时间里的都多(公园里一共有3个人找他搭话)。他烦恼的是周二没法来这里,“工作日挤不上年轻人的公交车”。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哪怕是雾霾天,只要赶上周二和周六,菖蒲河公园就不会缺少老人。尽管菖蒲河长达500米,但供老人们栖息的地方只有一个长约百米的长亭。长亭被老树环绕,到了冬天,枯叶飘零,老人们就在亭子里吃瓜子、打牌、闲聊。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捶腿。超过中午12点,亭子里很难找到座位,来得晚的老人干脆靠树站着,后背一次次撞向老树,以此来“疏通经络”。菖蒲河公园里交谈的老人们。图/网络在这里,不是所有的相亲都必须有个结果。年轻人之间相亲总得约个饭,加个微信,回头成不成还得搞清楚。但老人不是。许多事比相亲更重要,比如坐在热闹的老人堆里,心满意足地喝上一口泡满枸杞的热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身形日益佝偻的老人来到这儿,转型成为一个交际舞达人——舞伴很可能每次都不一样。跳舞跟相亲有关系吗?有,但不大。年轻人老了一个周六,阳光明亮,从东北方向照到菖蒲河公园里。从跃动的影子上,看不出是这一群老年人。这周的舞曲以《敖包相会》开场,又以《伤不起》结束,旋律穿越了60多年。中间放到蒋大为的《牡丹之歌》,一个路过公园的年轻人笑了,跟同伴说,“这群老人挺潮的,还听《五环之歌》”。菖蒲河公园里跳舞的老人。图/网络望着跳舞的人群,78岁的张秀芬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多了几丝神采。她说话有着老北京人的特色口音,强调某个字,会把音拖得又细又长。由于怕冷,她穿一件蓝色棉衣,裹着褐色的围巾。两用手推车放在10米开外的一棵老树下面,是用来当拐杖和买菜用的。老树下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手推车,主人们依靠颜色和车中的暖水壶来区分各自的车。张秀芬年轻时也用手推车,那时她刚18岁,和几个姐妹用车运炼好的钢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正上大专,号召大炼钢铁,天天不让学习,拿着耐火砖到处跑,炼出来一些黑铁坨子,兴高采烈地推着车,把黑铁坨子交给铁厂。现在想起来,那炼出来的是什么呀,能用吗?“她把“能”字拖得老长。那段时间她顾不上谈恋爱。“之后是四清运动和文革,我下乡到怀柔种地,更不敢谈恋爱了。”张秀芬说,如果当时一个女生跟男生多说了几句话,被人发现了,就是思想上有问题。在张秀芬的青春里,“爱情”这个词消失了。在菖蒲河,许多老人的恋爱经历都是缺损的。70岁的雷大同可能是少有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遇到过“真爱”的人。手里总是盘着核桃的他,说到激动的时候,盘核桃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当年一个女生热烈地追求他,“她约我一起去看《红色娘子军》。”他已经不记得几十年前女生的相貌了,但激动和喜欢的心情还留在记忆里。只是在故事的最后,一种更高层次的驱动力让他决定跟女生彻底断绝关系——“她家里的成分不好,我得划清界限。”女生后来老了,他也老了。两人相继有了家庭。到现在,雷大同的老伴去世3年了。他想起当年的她,托人打听才知道,她去年去世了。说到这里,雷大同手里的核桃停住了。人到晚年总有想要抓住点什么的奋力感。但面对彼此,老人们普遍不知道聊天怎么开头,自由恋爱要怎么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好感?怎么打动对方的心?对张秀芬来说,这些问题太难了。于是整日整日的,她只是坐在亭子北面的一个角落里,不主动跟人交谈,也很少有人来找她。等到太阳落山,她就拄着手推车,坐60路公交车回家。在雷大同眼里看来,张秀芬这个老太太“太闷了,过日子肯定没意思”。他更喜欢主动出击,看到新来的老太太就要上去搭话。恋爱的开场白通常是“你有什么条件”,或者是“你的条件怎么样”。他刚聊的一个老太太条件不错,住在东四,有自己的房子,女儿已经成年,孙子也已经长大——这跟他内心期望的条件完美吻合,“女儿意味着不用花费太多钱,孙子已经长大意味着不用带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意味着不用纠结婚后的财产分割”。但聊天进行10分钟后,他们不欢而散。得知老太太有糖尿病,雷大同就糖尿病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肯定是你以前糖吃多了,现在得了糖尿病”,老太太坚持说自己的病是因为遗传。雷大同毫不妥协:“肯定也跟你以前甜的吃得比较多有关系。”两个老人争执不下,几乎到了要吵架的地步。最后老太太站起来走了。雷大同本来还准备继续说下去,一时间嘴都没有合上,但声音却被掐断了。最后他叹出一口气。老年人的风北京的菖蒲河曾是一条消失的河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把河沟填平,改为街道。到了2002年的时候,又觉得还是河好,于是把居民迁走,重新挖成了河,建了亭台。唯一没变迁的是河岸边的60多株老树。最老的一株柳树,得两个老人合抱才围得住。这株老柳立在菖蒲河公园亭子的台阶口,见证了太多人来来去去。有的老人头两年还来,今年不来了,人们问起来,都说没人照顾,死在家里的床上;有的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伴儿,带回家儿子却不满意这个后妈,只能分了,又出现在公园里;还有的老人喜欢在除周二、六其他的时间来这里,这时候人少,可以在树下平静地打完一套42式太极拳。公园里需要两人合抱的老树。图/网络这株老柳成为菖蒲河公园中心区域的标志。中心区域自然用来跳舞。72岁的周铁军是最活跃的舞者之一。他会跳各种舞,比如交际舞、民族舞。通常,他会先独舞一曲,跳出一种一会儿像是蒙古舞,一会儿又像是藏族舞动作的舞。他把这些舞统称为“广场舞”,因为都是从不同地方的广场舞上学来的。独舞之后,他会领一个舞伴。比如这次,一个50多岁的戴墨镜、身穿鲜红衣服的女人约他共舞,他绅士地鞠了一躬,然后与对方自然地把手握在一起,肢体随着转动不时发生接触。“跳舞时的身体接触很重要。”这是周铁军用来培养感情的一种方式,不这样的话,他平时能握住的东西就只有茶杯。情欲可以催生感情,这样的原理在老年人中也适用。菖蒲河公园的潜规则是,聊得好,或是跳舞跳到一起的可以一起吃饭,吃完饭,到了夜里,就可以一起睡觉了。“大多数人都是有需求,才会来这里。”周铁军说的需求指的是性需求。这一年里,周铁军说自己已经和5个以上的女人睡过觉,从50岁到70岁不等。这些人大多是舞伴,而有的人则再也没有出现在菖蒲河公园。过去,周铁军最害怕下楼买菜遇到熟人,对方总会问一句,“最近过得怎么样”。那时他明明一个人过得很差,一日三餐都是楼下买的馒头稀饭,嘴巴上也要回应说,“过得挺好”。到菖蒲河公园后,跳舞的周铁军变了,他成了小区里主动问对方“过得怎么样”的那一个。对老人们来说,单身时间长了,很多事情也能够习惯了。比如一个人去药店买降血压的药,一个人推着手推车买菜,兴致来了一个人做出三盘菜,显得很丰盛的样子;又比如一个人望着窗外抽烟,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凳子上剥桔子,明明没人在意,却对着每一个认识的人大声打招呼。他们努力把生活过得很热闹,只是在某些时刻,现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无法抵挡的。比如有些相识的人可能明天就不在了;比如看到别的老两口成双成对地在楼下遛弯。这种不确定感近乎于一种恐惧,再顽固的老人也可能被改变。就像周铁军年轻时是个保守的人,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地上捡起一个粉红色的手帕都会脸红半天。现在他已经掌握在《自由飞翔》的旋律中,既把悄悄话传到舞伴耳朵里,又不让对方感到被侵犯的合适距离了。这种恐惧也改变了张秀芬。50多年前上山下乡,她是一个可以在寂静村庄的月光下插秧、被蚂蟥咬了就“撒点盐搓下来”的女汉子。现在她却可以为温度计摔碎了这样的事紧张不已。“那些水银珠在地上滚,是有毒的吧?我不敢弄它们,但不弄又不行,只能弄个毛巾捂住嘴巴,把温度计碎片扫走。”温度计摔碎已是两年前。但直到今年,张秀芬都在担忧,“你说那个水银温度计会不会有什么毒?对身体有害吗?”说这话时,一阵含着阳光温度的风吹过来,张秀芬打了个哆嗦。“年轻的时候感受到的风,和老了之后感受到的风是不一样的。”果然,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冰凉的。周铁军为了能活得久一些,多跳一些舞,专门参加了一些老年保健品的推广会。上个月,他花了3000块钱买了3盒“寡糖粉”。保健会上的人宣称,广岛原子弹爆炸,只有螃蟹活了下来,“这是因为科学家研究发现,螃蟹的甲壳里含有寡糖。”对方让周铁军花1万块钱买10盒,他将信将疑,决定先花3000块钱试一试,几乎花去一个月的退休金。回到家,儿子则说他“脑子进了水”。“年轻时不怕死,现在反倒怕了。”周铁军尴尬地笑了笑。但如果有什么事比死更让他害怕的话,那就是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自己身边。与时间谈判但凡在菖蒲河公园待上一阵的老人,都已经掌握能快速了解对方晚年经济状况的提问方法。“你住平房还是楼房?”——可以判断出对方是郊区人还是城区人。“你跟儿女一起住吗?”——跟儿女一起住的很可能没自己的房子。“你多少退休金?”——退休金每个月5000元是一条分界线,高的不会和低的谈。当社会上的相亲鄙视链传递到老人群体中,老人变得比年轻人要现实得多。年轻意味着可以试错,可以挥霍时间,可以充满可能,但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20年呢?有老人在地上摆上征婚广告。图/网络张秀芬剩下的时间可能更少。她已经78岁了,还有高血压、冠心病。她受不得风吹,总带着一个灰色的遮耳帽;她的手是冰凉的,因此总要放到手套里。她说,“我一生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菖蒲河又给了她一点念想。老人们之间相亲,更像是在与时间谈判,因此更难。他们在意的事情可以千奇百怪:一个吃鸡爪子把骨头吐到地上的老太太希望对方每天给她做饭;一个65岁的大爷希望找到一个高龄的处女;一个健康的老人希望说服对方跟他一起办残疾证,“去很多景点可以免费”。在菖蒲河公园晒太阳的老人。图/网络尽管要求千奇百怪,但子女的意见往往是决定相亲的最后一步。老家在河北的胡国庆在菖蒲河公园寻觅了半年之久。他60岁,很现实,就想找一个外地的年龄差不多的女人过日子,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但就是找不到。他离婚早,独自把女儿带大,也很宠爱女儿。这次出来相亲,也是受了女儿的鼓励。女儿对他说:“爸爸,你去找个伴儿,好给我带娃。”每次跟相亲对象谈到“要给女儿带娃”,对方就情绪大变。“谁要给你们家孩子带娃?过来相亲又不是受罪的。”像这样关于儿女的话题总能把气氛弄得很紧张。“儿女对你怎么样?”的问题不能随便问,因为来菖蒲河相亲的老人中有许多都觉得儿女不怎么样。有的老人尽管跟子女住在一起,但心的距离却隔得很远。在亭子里坐着的下午,总能听到一两个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大,“我那个儿子总嫌我在家里啰嗦,这下好,我自己搬出来住!”但搬出来住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那个抱怨儿子的老太太声音低了下去。她的老伴已经去世多年,现在一个人租住在10楼,一袋米吃了4个月还没有吃完。有一次电梯坏了,她走走停停,用了半个小时爬完楼梯。张秀芬是瞒着女儿来菖蒲河公园的。女儿已经40岁了,依然单着。她跟女儿都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安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避免她们被外界伤害的同时,也断绝了沟通的渠道。“我跟我女儿只要在一起,就像两只刺猬。”“女人到40岁还单身就完了。”正是出于对这个理论的恐惧,张秀芬当年才在38岁的时候急匆匆找了第一任丈夫。“谁都有老的一天啊。”她不想女儿步她后尘找个人凑合,也无法接受女儿的“不婚主义”。于是,在周二周六去完菖蒲河公园后,她改天还要去天坛公园给女儿相亲。女儿不让她管,说“妈,难道我会把幸福往门外推吗?”“不推你就赶紧找啊!”母女两人住在一起时天天为这事争吵。最后日子没法过了,张秀芬一个人跑到外面租房子住。她至今仍用一个黑白屏的手机,手机里只存了女儿的号码,每次想打,却又忍住了。她总是盼望着春节快点来,女儿,还有第二任丈夫的两个孩子,会理所当然地聚到她的出租屋里,一起吃个团年饭。这样的机会年复一年,逐渐减少。在菖蒲河公园坐得够久,总会等到散场的那一刻。如同一天的晨昏交接之时,时间在这时候迅速衰老下去:音乐戛然而止,跳舞的老人一时间待在原地,打牌的老人看不清牌面,聊天的老人意识到得赶紧回家买楼下的热馍。刚才还生机勃勃、做着各种事情的老人们,一瞬间变成了相似的样子——眼神里的光彩消失了。他们纷纷把腰弯下去,拄着手推车,掏出老年证,一步一步朝菖蒲河外走去。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公号(ID:meiriren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