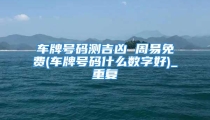何国强的左臂上,文着“1994.11.17”的字样,时间久远,当年的纹路已成青绿色。他说,那天是他走进派出所接受调查的日子,刻骨铭心。何国强的左臂上,文着“1994.11.17”的字样,他说,那天是他走进派出所接受调查的日子。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那天开始,何国强被羁押,他被控参与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两名出租车司机被害于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河北承德,此案影响巨大。承德市警方在侦查中认定,嫌疑人是大石庙乡庄头营村的青年陈国清、何国强、杨世亮和朱彦强。之后此案经历了长达10年的”马拉松”审理。承德中院三次以”抢劫罪”判处四人死刑,河北高院三次以”证据不足”等理由驳回四人的死刑判决,第四次,承德中院判处陈国清和杨世亮死刑立即执行,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2003年,河北高院二审将陈国清、杨世亮改判死缓。在狱中,四人一直坚持申诉,称自己无罪。媒体以”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为题对此案进行报道,此案甚至作为”疑案”案例,进入了大学课堂。被判死缓的何国强在前后减刑5年11个月后,于2021年3月3日刑满释放,其他三人仍在狱中服刑。何国强算着日子,他共被关押26年3个月14天,从22岁到48岁,从青年到中年。出狱后的何国强变得沉默寡言。他认为自己冤屈,但情绪已经不强烈。他说,申诉是他的终生目标,他还要融入社会,娶妻生子。出狱不到一个月的现在,他在努力适应现代生活。归家由于城中村改造,何国强的老家庄头营村在2010年消失在了地图上。回迁房在去年分了下来,但何国强的父母没住进去,总想盼着儿子回来再说。目前,他们暂住在山上的三间临时工棚里。出狱后的何国强光头,眼角有明显的褶皱。他中等个头,大臂粗壮,习惯性地挺直腰背,胸肌显露出来。刚回来那几天,何国强坚持晚上要和父母睡在一间房里。他说自己回家20多天,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每晚得醒四五次,心脏也不好,感觉就是心口扎得慌,刺痛。”他现在仍保留着监狱里的作息习惯,每天6时30分起床,之后就绕着山跑步。”恢复恢复体力,越不锻炼就越没劲。”出狱后的体检查出高血压,他一直没吃降压药,因为”一吃就不能停。”他琢磨着,跑步兴许能降血压。“我的身体内脏,各个部位和关节,都有点跟不上节奏。”他说自己走路时,小腿肚子和脚腕子就发疼,”在监狱里呆了26年,太虚了。”右脑蛛网膜囊肿则是老毛病。何国强回忆,初次发现脑壳里长了”水泡”,是有天他昏倒在厕所,送去医院查出了囊肿,已经压迫到血管。出狱之后他去复查,这个”定时炸弹”依然在,而且由于靠近血管,做手术也有风险。失去自由那天,何国强虚岁22,婚房刚盖妥,还没成家,是父母眼里的孩子。出狱的时候,何国强48岁了,孑然一身,在父母眼里,仍然是孩子。母亲付玉茹要求儿子出门带着她,”就像孩子丢了27年似的,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我得盯紧他。”山上风大,何国强喉咙发炎,用手在脖子上揪出紫红色的痧,付玉茹就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带药上山。中午阳光正好,何国强罩上有年头的蓝工装,给父亲何占一染白头发。何占一围上旧床单,低头坐在儿子面前,常年皱着的眉头舒展开,表情顺从。何国强给父亲何占一焗油理发。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工棚在燕山腹地,窗外贴着防风的塑料膜,三月气温回暖,阳光照进破木板围成的小院里。常年的风吹日晒,令何占一的脸变成了灰棕色,眼睛遇到风就会流出泪水。儿子离开的这些年,他常常借酒消愁,整个人瘦得像干柴一般。焗油染发的手艺,是何国强在监狱里练出来的。他回忆,刚进去时,他年轻,学东西快,就给老干警理发。很快他就能用推子理寸头了,后来染发焗油都不在话下。何国强熟练地拿起推子,把父亲后脑勺和耳旁的头发打薄,把头顶的头发梳成偏分。大妹在一旁看着,建议哥哥去理发店打工。但何国强对进入社会还没有信心。”自己与社会太脱节了,一两年之内应该干不了啥。”他说,熟悉的地点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以前都是小瓦房或者小草房,房子里自己生炉子或者生大灶子,现在都住楼房了,给我领到我们老家那里,我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何国强回家后,山腰上的棚屋热闹了起来。不时有亲戚朋友登门看望,何占一在圆桌上摆了过年时才启用的黄铜火锅,付玉茹忙里忙外准备餐食,何国强帮助打扫,在席间,他为客人倒酒,主动碰杯感谢,努力做到周到。亲戚送给何国强一台苹果手机。用了两个星期,何国强学会了用微信接打电话。但仍记不牢自己11位的手机号码。何国强不习惯用手机键盘敲字,就用手写打字,智能手机对何国强来说仿佛科幻。他回忆,1994年自己”进去”之前,固定电话都很少见,BB机是新潮和有钱的象征,”掌中宝”和”小灵通”更是听过没见过。何国强掏出一副黑框眼镜戴上。“眼睛都花了,这150度的。”他语气中带笑,像在自嘲。”现在是眼睛也不好使,腿也不好使,出门就绊跟头。”他把手机举到眼镜前,这才看得清字。何国强戴上了老花镜看手机。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眼花是中老年人的普遍症状,但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总在光线不好的屋里关着,他不会眼花。他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划开微信,点开与妹妹的对话框,那里有一段给小外甥女录的视频。小姑娘看着镜头,喊着”大舅”,与他”唠嗑”,憨态可掬。何国强看着看着,忍不住笑了起来。遗憾夜晚,何占一在家门口亮起红灯笼,寓意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生活的色彩吸引着何国强,他很少主动提起那些灰暗的日子。何国强关灭手机,轻轻地说,被羁押时,”想法简单,只是想喊冤”。“看守所就是个仓库。”何国强说,作为被判死刑的重刑犯,他单独关押在监舍里,只有被提审时才能见到人说话。那是被时光固定住的10年。在监狱的16年,则”像是进了工厂”。他成了监狱里的技工,赚积分,赢得了7次共5年11个月的减刑。他还做过勤杂工,给办公室打扫卫生,帮助食堂开饭。“那饭桶100来斤,我们俩人一抬。”他展示粗壮的大臂肌肉。在旁人看来,近27年的牢狱时光,把何国强”磨平”了。这或许也是他”积极改造”的结果。但至今,何国强仍不认罪,他认为,这场牢狱之灾成了他整个人生的遗憾。“多大的遗憾啊你说。我本身就是守法的公民,背着一个没犯过的罪,你琢磨琢磨,一般人体验不到这种地步的遗憾。”他称,自己当时被迫认罪,试图自杀了好几回。2003年在河北高院终审开庭时,四名嫌疑人均坚称被刑讯逼供,法官同意了四人当庭验伤的要求,但在最终判决时,未认定有刑讯逼供。何国强脱下裤子,给记者展示大腿上的伤疤。经过岁月的打磨,那些一条条、一块块的疤痕已经变淡,如浮雕一般凸起在皮肤上。当年的破案报告记载,警方在陈国清家中提取了一把自制单刃匕首,匕首刀把上残存着一粒米大的血痕。血痕检验与其中一名被杀司机的血清型相同。警方又在另一名被杀司机的出租车中找到了一截烟头,鉴定出上面唾液斑与杨士亮的唾液是同一个体的准确率为99.06%。这些鉴定报告及认罪供述,成为四人被判有罪的主要依据。陈国清的辩护律师吕宝祥已经年过八旬,他告诉记者,每次河北高院发回重审,都会给承德中院列一份《发还提纲》,里面列举了此案的疑点,三份《发还提纲》列出的疑点不下20个,其中包括对赃物下落不明、有无作案时间、被告人翻供、出租车上遗留财物去向、在押犯揭发说疑似作案凶手等情况的疑问。吕宝祥还提到,陈国清先被抓获,然后”咬”出了何国强、杨世亮和朱彦强。”陈国清招了一、二十人,警方在他们村抓了几十个人。为什么其他人线索都断了?”“这些疑问都无法排除,所以最后的判决也留有余地。”吕宝祥认为,此案应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教授何家弘曾带领学生们讨论此案证据中的疑点。“在陈国清等人涉嫌杀人案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有罪推定的痕迹。”何教授指出,如果价值取向是打击犯罪,那就会确立有罪推定原则;如果价值取向是保护人权,那就会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何国强说,自己一直坚持申诉。何国强和父母在一起。从他被羁押开始,家人就踏上了信访和申诉之路。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付玉茹说,从儿子被羁押开始,她和另外三家的家属就踏上了信访和申诉之路。“火车票都那么高一摞。”付玉茹用手比了个和视线齐平的高度。她说,为了省钱,住十元钱的床位。”回家一脱衣服,黑秋衣上白花花的全是跳蚤。”付玉茹说,令他们家人遗憾的是,在2020年12月28日,即何国强刑满出狱前两个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不予抗诉的决定。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交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称,经复查认为,此前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审判程序及量刑上并无不当”,”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本院决定不予抗诉”。空房子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那天,一名记者拍下了何国强被押在警车内的照片。何国强当时32岁,已经被羁押九年半,他头上还有黑发,脸庞尚且圆润。他从警车内望向窗外,满脸迷茫。今年,何国强48岁了,迎来了本命年。按当地风俗,本命年要小心行事。付玉茹给儿子置办了一套黑衣服,还决定让儿子在未来一年待在家里,”不要太折腾了,好好恢复身体。”出狱后第三天,何国强去给爷爷上坟,他摆上家人准备的水果,烧了厚厚一沓纸钱。何国强的爷爷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何占一是长子,负责赡养老人。何国强跟着爷爷长大,祖孙俩睡同个被窝,在一个盆子里洗头洗脚。何占一说,父亲是一级厨师,退休后,有着稳定的退休金。而他自己年轻时在农业研究所打过工,掌握种菜的技术,和妻子付玉茹经营两个蔬菜大棚。”别人种菜一般两季,但我能收三季”。拆迁之前,庄头营村靠近农贸市场,何占一种的黄瓜比别人更早上市,销路也好。他记得1994年夏天,也就是儿子出事那年,黄瓜丰收,他们全家没日没夜地摘黄瓜,”怕烂在地里,我们天不亮就起来,拿着手电筒,一上午能摘200斤。”按一块多一斤的批发价,他能卖200多元钱。何国强和父母如今住在山腰的临时棚屋里,周围是一片工地和工厂。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根据警方调查,歹徒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后,共抢走了几百元现金和两个BB机。何占一至今不相信何国强犯案,因为这些财物价值不及他家几天的收入。也是那一年,何占一花五万元盖了新房,准备给21岁的儿子娶媳妇。他说,那是”非常豁亮”的4间平房,地下还有5间储藏室。房子盖好了,正在张罗装修,”从唐山运过来的小瓷砖刚贴上”。何国强初中上了几天就辍学,之后跟着古建队学手艺。何占一说,新房子的门窗是儿子亲手打的,他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刚把门窗的玻璃装上,就”出事”了。“新房一天没住上。”何占一说,儿子被带走后,老两口把新房住成了旧房,2010年,双桥区城中村改造,庄头营村和农贸市场都拆迁了,他们就搬到了山上的棚屋。由于耕地也被征用,何占一和付玉茹每月有2000元养老金,他们花100元在棚屋旁租了一块空地,自己种了玉米,还有葫芦、黄瓜、土豆、韭菜等蔬菜,他们还养了四只母鸡、五只公鸡和几头羊,在吃饭上自给自足,把花销控制到极少。这些年,城市变化巨大,堵车、高楼、高架桥,甚至暖气片都让刚出狱的何国强感到陌生。但回到山上,他有了熟悉的感觉。何国强父母用的家具全是旧的,何国强爷爷传下的家具仍然摆着。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因为节俭,这近30年的时光里,老两口的生活冻住了。家具全是旧的,何国强爷爷传下的家具仍然摆着,那是一台抽屉松动的木桌,和两口磨出釉面的大箱子,而一旁的老衣柜玻璃已经全碎,用棉布包着,也是上个世纪的物事。拆迁后,何占一家分了五套回迁房。他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套,给自己老两口和儿子留了三套。回迁房在高档小区里,有个复杂洋气的地名,老两口没张罗装修。他们空着新房子,总算把儿子盼了回来。婚事刚回家时,何国强哭了几场,后来他总是眉头锁着,看起来心事重重。他经常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一天早晨,他自告奋勇要拖地。涮拖布时,本应用院子里清洗拖布的水桶,他却随手把拖布放进了浇菜用的大水缸。付玉茹翻出了何国强的信件,里面有过去的朋友寄到看守所的,也有他在狱中写给父母的。何国强读了一会,就把这些信都扔到灶台里烧了。何国强读完被羁押时的信件,把这些纸扔到灶炉里烧了。新京报记者苑苏文摄对自己的案子,何国强总是敷衍地说”时间太长,记不清了。”付玉茹陪在一旁,忍不住替儿子表达心迹:”在看守所时,他恨不得提前开庭,把冤屈说给法官。”但现在,何国强记忆里只剩下失望的感觉。”要不就是开庭,再发还,再开庭,再发还,总是给点希望,然后又破灭,给点希望又破灭,一直到我出监。一直这么着。”他说还是要继续申诉,但在青春耗尽的当下,他更多的动力是为了下一代。”等我有了孩子以后,人家再说他爸爸是杀人犯……”他停顿了下,似乎又有点不确定,”你说我背着杀人犯的名声还是会影响下一代,是不?”付玉茹说,儿子回来后,总是在床上一坐就是半天,问他在想什么,他又说不出,”好像整个人是空的”。何国强提起,同龄人都有了第三代,自己被耽误了。“如果不坐牢,你的生活会怎样?”记者问。“会过上平凡的生活”,“什么是平凡的生活?”“有家庭有孩子,有一份体面的事业。”为了给唯一的儿子何国强成家,他的老父母把这些年的养老金都存了起来。但在当下,婚事还需要时间。两年前,何国强还在狱中时,一名离异的女士开始与他通信。出狱那天,这位女士去接了他,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位女士今年39岁,两人通信时的感情真挚而热烈。何国强把手机屏保和微信聊天背景都换成了她的照片。女士提出订婚,这难倒了何国强的父母。“我们欠了几十万的外债,装修房子的钱都得借。”付玉茹不敢当着何国强的面讨论这桩”喜事”。按习俗,订婚时要给女方6万彩礼,还要准备”三金”。老两口盼着何国强结婚,但问题也许出在”幸福来得太突然”。付玉茹担心,何国强刚刚出狱,两人都还不够了解。但何国强坚持认为两人合得来,并劝母亲”我这样的也找不到别人了。”于是,付玉茹只好一边建议”再处俩月”,一边借了钱让何国强装修房子。和女朋友聊天时,何国强的话就多了起来。吃完午饭,山上阳光正好,何国强把手机端在耳旁,在院子后面溜达着和女友通话。他眼睛里有了神采,语气温柔。记者苑苏文实习生梅云秋编辑胡杰校对卢茜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