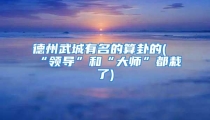有唐一代,中西交通大开,国力强盛,加之统治者锐意经营西域,大量的西域胡人循着陆海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这其中包括波斯人、粟特人、吐火罗人及西域诸国人等。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学界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活跃在中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波斯人的入华活动因史料的缺载,关注较少。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大文明的中心,中国文明和波斯文明有着较早的渊源关系,至少在西汉时期,西亚的帕提亚王朝(PathianEmpire,即汉文史籍中的安息王朝)就和汉王朝有了通使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其后萨珊波斯王朝兴起后,更是与东方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其中北魏、隋唐时期都是双方交往的密切时期。而波斯人真正的入华活动,则是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高潮,因而通过对唐代入华波斯人及其活动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两大文明本源,即中国与波斯之间的交流,以及波斯人的入华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等。关于这个问题,荣新江、张广达等先生对此有过较为细致的探讨与研究,[1]但仍有要补充与讨论之处,本文即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爬梳整理相关资料,尝试勾勒出这一时期入华波斯人的分布及活动情况。一、隋唐与萨珊波斯的交往及波斯人入华活动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西尔一世(ArdashirI)杀死了帕提亚(安息)王阿尔达汪五世(ArdavanV),攻占了其首都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波斯萨珊王朝,此后直到公元651年波斯末代主伊嗣俟被大食所灭,萨珊王朝从此灭亡为止,这个王朝存在了四个多世纪,时间上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时期。在这段时期波斯帝国与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和交往,有不少波斯人循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约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北魏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2]中国和西亚自两汉以来在中断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了直接交往,此后直到西魏废帝二年(553),波斯使者到访西魏都城长安为止,[3]波斯和北魏、西魏、南朝梁等都有通使往来,其中和北魏的通使就有近十次,和梁朝通使约有三次。[4]现存南京博物院梁元帝萧绎所绘的《职贡图》宋摹本中就有波斯使者的形象及相关题记。[5]当时所谓的交流盛况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6]虽然指的是北魏情形,但也说明南北朝时期西亚与中国交往的频繁。隋朝建立后,统一南北。隋炀帝即位(605)时,海内晏平,国富民殷,加之炀帝本人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积极从事疆土的开拓,又开始了对西域经营。炀帝即位初,即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及中西亚诸国,“至罽宾(今克什米尔)得码碯杯;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之拉杰吉尔)得佛经;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7]至安国“得五色盐而返”。[8]除此之外,炀帝时,又曾遣使出使波斯,如《隋书·西域传》载:波斯王库萨和时期“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9]有学者认为李昱有可能是同韦节等一起出使的,这个使团在途中分为两路,一路以韦节为中心南下印度,另一路以李昱为中心赴伊朗地区。[10]这里提到的波斯王库萨和,当即波斯国王库斯老二世(ChosrauⅡ),李昱出使的目的应与韦节等相同。总之,李昱还是顺利到了波斯,波斯亦派使者随李昱前来贡方物,双方的政治交往又重新建立。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炀帝大业年间(605—618)“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州县,疲于迎送”。[11]当时来朝贡贸易者达三十余国,隋专门设“西域校尉以应接之”,[12]这其中应有韦节、李昱等出使宣扬国威及进行贸易原因。当时的来隋朝贡贸易的包括西亚的波斯,还有属于波斯地区的乌那曷(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之巴尔赫Balkh)、穆国(即木鹿地区,今土库曼斯坦马雷Mary)等。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因炀帝暴政,几年后天下大乱,隋也就灭亡了,经营西域的事业也如昙花一现,这种情形至唐才有所改观。唐朝初年,波斯萨珊王朝已日益衰败。在唐高宗灭西突厥,统一西域,并在葱岭东西设置羁縻府州之时,西边大食(阿拉伯)开始了向东扩张的步伐,其很快就将触角伸向了日渐衰落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632年,波斯末代主伊嗣俟(YazagardIII)继位,随后就受到来自大食的攻击,公元651,伊嗣俟被大食击败,逃到吐火罗境内的木禄(木鹿)城,很快被杀,萨珊帝国灭亡。据《新唐书·西域传》云波斯末代王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而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13]波斯为大食所灭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王子曾避难吐火罗,并遣使于唐告难,但高宗以路远没有答应出兵。高宗龙朔初年(661)又遣使告难,此时正值高宗遣使在西域一带建立羁縻府州时期,当时高宗派遣王名远到吐火罗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其后以疾陵城(今伊朗卑路支-锡斯坦省东北)为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但没过几年,波斯很快就被大食吞并。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卑路斯等避难前来长安,授右武卫将军,后客死长安。高宗调露元年(679),其子泥涅师师(Narses)在唐军护送下归国复辟,没有成功,寄寓吐火罗二十余年。中宗景龙二年(708),又返回长安,授左威卫将军,后也客死中土。[14]从某些方面来说,自北魏以来,就应有不少波斯人来到中国,以洛阳为集中,这其中既有使节,也应有不少随时节而来的波斯商胡。隋炀帝招募西域,也有不少使节商人等东来,而波斯人真正的入华活动则在有唐一代达到高潮。波斯的使节自太宗贞观年间始就数次遣使朝贡,高宗时期虽然国灭,但遣使活动仍然进行,大概有七次之多,玄宗时期更是达到高峰,史载约有16此之多,一直至代宗时期大历,遣使活动才中止。[15]所谓自高宗时期开始及以后的波斯遣使活动应是波斯余部及后裔等进行的,但仍以波斯的名义进行。随着波斯使节大量来到中国,有很多人即长留不返,定居中国;此外随着使节而来的波斯商胡等亦有不少,其中有些本身应该是商胡冒贡使之名而来,他们也将足迹印在中国大地。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随卑路斯父子而来的波斯王室后裔,人数不会少,多寄寓中土。如高宗仪凤二年(677),卑路斯请求在长安醴泉坊设波斯寺,[16]在其周围应有一大批波斯皇族或贵族后裔。此后陆续又有不少波斯人来长安,这些人中除使节、官员外,还有不少宗教僧侣及商人等,这显然与唐代海陆交通的发展及国力强盛、社会开放等有很大关系。二、唐朝境内的波斯人及其活动唐朝境内的波斯人,除却一部分可能是自北朝时期来华的波斯人及其后裔,大部分应是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中西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范围,陆路方面多在丝路沿线,以两京地区为集中;海陆方面则主要集中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等地。下面我们按地域来论述。两京地区:这是波斯上层人物最集中的地方,尤以长安为主,这其中就包括波斯萨珊王族后裔们。例如:萨珊波斯王子卑路斯及其子泥涅师师等:波斯为大食所灭后,王子(波斯末代主伊嗣俟之子)卑路斯于咸亨年间(670—674)避难前来长安,授右武卫将军,后客死长安。其子泥涅师师在唐军护送下归国复辟,没有成功,寄寓吐火罗二十余年。中宗景龙二年(708),又返回长安,授左威卫将军,后也客死中土。随卑路斯父子而来的波斯王室后裔,人数不会少,多寄寓中土。如仪凤二年(677),卑路斯请求在长安醴泉坊设波斯寺,此波斯寺一般认为是景教寺院,[17]说明其周围有一批波斯景教徒。其间或其后陆续又有波斯人来长安,如南昧,乾陵石人像右二碑第三人的衔名为“波斯大首领南昧”,陈国灿先生认为其可能是与卑路斯同来长安的波斯大首领。[18]穆沙诺:波斯首领。《册府元龟》卷975载:开元十三年(727)七月及十八年(732)十一月,波斯首领穆沙诺两次来朝,“授折冲,留宿卫”,[19]未注明要“放还蕃”,说明其在长安任职,开元年间到来的波斯首领应该不是来自波斯本土,从穆姓来看,应该是与原波斯东境的末禄国(即木鹿地区)有关。苏谅及其妻马氏:1955年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配合基建中,于西安西郊约2公里的土门村附近发现一方《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志石。志石上半刻有一种波斯文字,横书六行;下半为汉文,直书七行。汉文志文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已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874)甲午□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巳申时身之故记”。墓志外国文字部由当时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博士作了研究,伊藤博士确立志石外国文字部分为中古波斯语之巴列维文,刘迎胜先生对伊藤氏译文中拉丁转写的若干错误进行重新认读,加上外国学者研究校正的拉丁转写录出,其志文翻译如下: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asis),于已故伊嗣俟(Yazakart)240年,及唐朝之260、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往)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20]阿胡拉·玛兹达为祆教之主神,志文说明苏谅及其妻马氏均为祆教徒,且都是波斯人,在其去世之时,仍使用波斯纪年。祆教本很早便流行于波斯及中亚一带,曾被萨珊朝立为国教,7世纪中叶,大食灭波斯,许多祆教徒东移,唐时长安、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祠宇,并置有萨宝府这一管理祆教的机构。武宗会昌五年(845)毁佛运动,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亦受禁止。武宗死后,禁止才解除。此碑立于咸通十五年(874),正是祆教在会昌被禁后复盛的时代,苏谅及其妻马氏这时期仍旧坚持其祆教信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苏谅妻马氏死时为年代距大食灭波斯(651)已200余年,但其西部仍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开元、天宝间继续有使者来华。在长安的波斯人仍继续使用波斯文字,信仰波斯国教。李素及其家族:1980年,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李素墓志》志文云“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公本国王之甥也……祖益初,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止卫中国,列在戎行。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袋,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父志,皇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公即别驾之长子也……(公)得裨灶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大历中,特奉诏旨,追赴阙庭……三年在内,累授恩荣,蒙敕赐妻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兼赐庄宅、店铺,遂放还私第,与夫人同归于宅……四朝供奉,五十余年,退食自公,恪勤无替。夫人有子三人,女一人,长子及女早岁沦亡。至贞元六年(790),不幸夫人倾逝。仲子景侁。朝请大夫试太常卿、上柱国、守河中散兵马使;季子景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晋州防御押衙……以贞元八年(792),礼聘卑失氏(突厥族),帝封为陇西郡夫人。有子四人,女二人,长子景亮,袭先君之艺业,能博学而攻文,身没之后,此乃继体;次子景弘,朝议郎试韩王府司马;少子景文,前太庙斋郎;功子景度,前丰陵挽郎……公往日历司天监,转汾、晋二州长史,出入丹墀,栖翔凤馆……时元和十二年(817)岁次丁酋十二月十七日终于静恭里也,享年七十有四……今于万年县浐川乡尚博村观台里,用置茔垄,时元和十四年(819)已亥岁五月戊寅朔十七日甲午迁葬于此……”。荣新江先生对此墓志做过深入研究。从志文上看,李素祖父益初,自天宝年间(742—756)奉波斯王命,来唐出使,因纳质子,宿卫长安。事实上,天宝时波斯已是阿拉伯帝国一个省份,不可能有自立的国王遣使入唐,且按唐代制度,都是蕃王之子在唐为质。故李素不应是国王外甥,而应是国王之胤。从其祖、父两代的汉化姓名来看,李素家族应该很早的时期就来到中国。从唐初以来,唐朝就把大量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隶属于中央十六卫大将,宿卫京师,李益初,大概就属于这类波斯人。[21]李素自幼随父在广州生活,大历中,因对天文星历之学的专长而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监,前后共50余年,经历代、德、顺、四朝,最终以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身份,卒于元和十二年(817)。其诸子在长安及附近关内道和河东道任职,有的甚至成为乡贡明经。[22]景教僧及烈等:前述李素家族就是来自波斯的景教徒。荣新江先生根据李素字“文贞”,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的僧侣名单中找到了“Luka/文贞”,同时联系李素的六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景”字,判定这是一个来自波斯的景教家族。[23]除此之外,长安斯景教僧还有不少,有一些是跟随波斯末代王子来华的波斯贵族,还有一些是其后入华但身份不明者。如开元二十年(732)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24]荣新江先生认为这里提到的大德僧及烈,以及建立的《景教碑》的景净和列名其上的许多景士,实际都是波斯人,说明长安的景教一直都是有波斯的教士维持着。[25]洛阳波斯王族后裔:二十世纪初洛阳出土有波斯人《阿罗憾墓志》。据志文载,阿罗憾为“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高宗天黄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招至来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驰。又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26]据学者研究阿罗憾是萨珊波斯王朝的王族,也可能是前波斯王库萨和的孙子,比波斯末代主伊嗣俟晚不了几年,公元651年伊嗣俟被杀,其子卑路斯逃亡吐火罗,阿罗憾当时大概随卑路斯一起活动,因其在西域威望,被高宗遣使召至长安,授将军北门右领使等,[27]显庆四年(659),被唐充拂林诸蕃诏尉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鉴于此时波斯大部分已被大食占据,断不能逾波斯而西,此拂菻西界,应指吐火罗地区。有学者指出阿罗憾出使拂菻(这里指吐火罗)与王名远在吐火罗立碑,实为同一历史事件,所谓拂菻诸蕃,其实就是吐火罗诸蕃,阿罗憾实际上就是吐火罗诸蕃招慰大使,[28]笔者同意这个看法。由墓志铭文可以看出,阿罗憾这次招慰是成功的,“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前述王名远在显庆龙朔年间出使册封活动中,对于吐火罗的一些府州的册封,有些大概是由阿罗憾来完成的。阿罗憾应是在完成任务后,和王名远返回唐朝复命。据墓志可知,武则天延载元年(694),阿罗憾还曾为武则天造立天枢出资出力。后因功被封为为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睿宗景云元年(710)以九十五岁高龄卒于洛阳私第。除此之外,两京地区亦活跃有不少波斯大贾。如波斯商人李苏沙:《旧唐书》记载穆宗长庆四年(824),有“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29]其李姓应为后来所改之姓,李苏沙大概是宫廷御用商人,从其进贡“沉香亭子材”,可知其经商规模不小。《乐府杂录》亦中记载有康老子,本“为长安富家子”,因家产荡尽,遇一老妪持一旧锦褥卖,康以米一千换来,后碰一波斯人,见褥大惊,云此乃冰蚕丝所织,酷暑时放于坐上,可致一室清凉,于是波斯人酬康千万,将其买去。[30]虽然此处所载多为野史,但多少也反映出波斯胡人的经商与鉴宝能力。另外在西域商人最集中的长安西市还有波斯邸,《太平广记·杜子春》条云:“杜子春,盖周隋间人……方冬,衣破腹空,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老人曰: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31]波斯邸大概是波斯人经营的邸店,或是停驻波斯等商胡的地方。东市的胡人店肆也有不少,如毕罗肆及买胡琴者,大概就是由西域或中亚的胡人来经营,这其中亦有由波斯人经营的店铺。如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云:“东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奶妪将煎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纸标,得一个饼。儿童奔走抛砖瓦博煎饼,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他皆效此,由是致富”。[32]所谓停波斯,大概是停驻波斯之意。说明唐长安东西两市皆有波斯胡人经营的店肆,而且颇有声望,往往成为地标性建筑。西南地区:有唐一代,巴蜀地区也是西域胡人活跃之地。南北朝隋唐时期,自西域通商入蜀的胡人是不少的,如何妥家族。据《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陈寅恪先生认为“西城”是“西域”之误。[33]何妥父为细胡,[34]可以推知何妥家族应为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何国人,萧梁时自西域入蜀经商,家于郫县,因事梁武陵王纪,主持商业贸易,因此成为西州大贾。这个家族至隋时还见于记载。《隋书·何稠传》载:“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兄之子也……稠性偏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至长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帛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即成,逾所献者,上甚悦。”[35]善织波斯锦的何妥家族虽然在隋朝时迁至长安,但肯定有不少西域商胡仍留在蜀地活动,这其中也应包括有不少波斯胡人。虽然关于唐代巴蜀地区波斯人记载较少,但晚唐五代的一些材料仍可以看出波斯人在蜀地的活动轨迹,尤其是晚唐及前蜀、后蜀时期,有一些波斯人后裔活动于此。比较著名的有李珣家族,清彭遵泗《蜀故》载:“梓州李珣有诗名,其先波斯人,事蜀主衍,妹为衍昭仪,亦能词,有‘鸳鸯瓦上忽然声’句。珣秀才预宾贡,国亡不仕,有感慨之音”。[36]又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亦载:“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人也,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文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37]可知李珣家族在前蜀地位不低,李珣为蜀主王衍宾贡,其妹为王衍昭仪,二人均有诗名,善词藻。其弟李玹仍延续六朝隋唐波斯人往来经商的传统,以贩香药为业,但文学艺术修养很高。这里的李珣家族应为唐末随僖宗入蜀而后客居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波斯人,其家族先与唐朝关系密切,客居蜀地后继而与前蜀王室关系密切。[38]除此之外,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南平政权内,也有一些关于巴蜀地区著籍的波斯人的活动记载。如宋路振《九国志》载:“(石)处温,万州人,本波斯之种,任前蜀为利州司马。同光中(923—926),知祥入蜀,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检指挥使,率义兵同收峡路”。[39]据此可知石处温为波斯人后裔,在前、后蜀都为官。另《宋高僧传》载:“巴东……有穆昭嗣者,波斯种也,幼好医术,随父谒之,乃画道士乘云……穆士后以医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令其去道从儒”。[40]此穆昭嗣,显为波斯人后裔,也是以医术而闻名,与南平王高从诲关系密切,不过从南平王令其去道从儒之事来看,其汉化很深,其祖上至少是隋唐时期来华之波斯人。穆昭嗣善医术之事在笔记小说中亦有反映。《太平广记》载:乾宁初“秭归郡草圣僧怀浚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胡卢,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41]可见穆昭嗣其人在晚唐五代时期以医术而闻名天下。总之,晚唐及五代十国政权范围内也存在着一部分波斯人、粟特人的后裔,他们多是由唐末迁来,也有一些著籍者,以巴蜀地区为多。其中中亚粟特人后裔多入仕于十国政权,波斯人后裔则更多以经商等为业,从事香药贸易与医药医术等方面的活动。尽管史籍缺载,但仍可看出中西亚胡人活动范围之广,至五代时期亦不例外。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畅通及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等地也聚集不少胡商,主要以扬州、广州为集中。杜甫有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42]可知扬州一带是当时商胡通商之地。据《旧唐书·田神功传》载:“(田神功)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略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胡商波斯被杀者数千人”。[43]可知扬州一带确实聚集不少商胡,从“胡商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知,这些商胡中应有不少波斯人。2015年扬州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唐代波斯人的墓志,该墓志据说是2004年在扬州古运河畔南宋普哈丁墓园南侧发现的。据墓志载:“府君世钦颖士。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舟航赴此,卜宅安居……于大和九年(835)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之私第,时七十有五矣”。[44]该墓碑是扬州发现唐代有姓名可考第一位波斯人。从墓主人父亲及其本人所称的“罗呼禄”、“摩呼禄”上看,其汉化并不深,但其使用汉文墓志,碑额题为“李府君”,又谓“世钦颖士”,应是来华有两代了,李府君当为改姓。至于其身份,既是“舟航赴此,卜宅安居”,也应是晚唐时期自海路来华的波斯商胡。墓主人本人名“摩呼禄”,志文中记载其夫人为穆氏,“摩”、“穆”相通,应是来自中亚木鹿一带的波斯人,其婚姻仍属胡姓之间的联姻。摩呼禄家族应是晚唐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来华的波斯人。除此之外,此外在《太平广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扬州胡人识宝鉴宝的传奇,如《李勉》条载:“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今扬州)。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焉,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述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45]李勉故事反映了江南波斯人善藏宝识宝的背景。《太平广记》中亦记载扬州有波斯店,如“卢李二生”条记载:“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46]以上记载说明扬州是西域胡人聚集与贸易之地。有学者研究认为扬州作为中晚唐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是一个聚集了包括粟特、波斯商人和普通移民在内的大量异国人士的国际贸易都会。[47]广州作为南中国海的重要口岸,亦是胡人聚集之地,自海路来华波斯人应该不会少。唐时自广州经海路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义净至广州,曾“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48]也就是从广州搭波斯舶起程前往印度。开元天宝时期更多波斯人来华,据史载:当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49]可知当时广州是前往南中国海及印度的重要港口,波斯舶的盛行,显然与唐代中晚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波斯人更多地选择海路来到中国有关。广州亦有波斯邸,《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有崔炜者……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50]可知广州亦是西胡聚居买卖之地。以上仅是梳理了唐代波斯人及其活动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唐代波斯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等的活动还是集中在两京地区,尤以长安为集中,充分显示了唐代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这其中既有波斯皇族、贵族及官员,亦有波斯景教、祆教僧侣及广大的商胡,波斯胡人经营的店肆已成为长安市场的地标及招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沿海一带则是在中晚唐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商人,这里更多的一些泛海而来的波斯商胡们,他们人数之多,大概超过唐代自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胡人,且颇具气候,在扬州、广州都能看见特色的波斯店或波斯邸,其独特文化及影响波及到后世。三、波斯人及波斯文化对唐及以后社会的影响由上文所言,唐代波斯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京、巴蜀及东南沿海地区。其实有唐一代波斯人的活动范围远不止这些,只是相关情况缺载而已。唐代中西陆海交通发达,双方的政治交往又比较密切,虽然地域遥远,但双方的人员往来及文化交流还是在持续进行。唐代丝路沿线其实也多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如河西敦煌是陆上交通的门户,波斯人自西域东来,必要行径此地。敦煌文书中出现有“波斯僧”字样。如S.1366《年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51]此波斯僧,应是路过的波斯景教僧侣。此外张大千于1941年在莫高窟前沙中发现的《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提到了同甲授勋的263个人名及籍贯,其中有“波斯沙钵那二人”,据朱雷先生研究,此沙钵那二人或系避大食之侵逼而由陆路转入安西四镇辖境。因而应募充当镇兵,并因征戍多年而获得授勋。[52]此外唐宋笔记小说中亦有一些关于波斯商人在陕西扶风、江西洪州(今南昌)等地的记载。如《太平广记》记载“一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买方石得径寸宝珠,于是随船泛海而去”。[53]同书又载“洪州(今江西南昌),江淮之间一都会也……有一僧人……取一小瓶,大如合拳……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羜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54]又有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55]“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今江西南昌),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56]虽然笔记小说反映的故事多有虚构成分,但故事的发生地点则应是真实的。小说里提到的扶风、洪州(豫章)等地,既是交通路口,也是胡人的商贸之地。也许波斯胡人在这里只是匆匆的过客,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但这些零星的记载也反映出他们足迹的广泛。可以说,随着敦煌吐鲁番及文书及唐代墓志大量出土,我们有了更多对于中亚粟特人的认识,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承担者多是由他们进行,唐代的胡人其实也多是指代粟特人,因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介民族,他们与东方的交往更为密切,他们的足迹也更多在出现在丝路沿线。但不能否认,作为丝路西端的文明大国,波斯人及其文化也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至东方大地,不管是对唐代或是后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至少波斯人及其文化象征更深入人心。首先波斯人可以作为西域胡人的代表。虽然唐代来华西域胡人以粟特人(昭武九姓)为多,但在唐代文献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很多关于九姓胡的记载,反倒是更多地看到“波斯寺”、“波斯邸”、“波斯胡人”等的记载。随着高宗时期波斯流亡王子及其大批随从来到中国,他们活动及唐朝给与的优养待遇本身给唐人留下深刻印象,高宗应卑路斯之请在醴泉坊设波斯寺更能反映了他们的地位之高。此外,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波斯邸往往成为商贸场所的代称或地标性建筑,以致唐人约定长安西市见面地点,往往是候于“波斯邸”等。而波斯商胡则是唐代商贸要道及繁华的大都市中的商业形象的象征,在沿海一带尤其活跃与突出,以致至唐末五代宋初的文献中还会提到波斯人等。南宋时期禅僧赜藏主持编撰《古尊宿语录》,记载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禅师语录云:“昆仑渡海夸珍宝,波斯门下聘须多”,[57]蔡鸿生先生指出这里说的昆仑乘舶渡海,携珍宝到汉地兜售,犹如波斯胡多须,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58]五代末陶谷的《清异录》记载南汉后主刘鋹之事“刘鋹昏纵,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59]南宋庄绰在《鸡肋篇》提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60]这里提到的波斯妇已与唐代来华伊朗系波斯人有了很大区别,可能是指南海一带的妇女,但波斯人的经商及泛海能力使得这个民族概念深入人心,以致唐及以后在内地及广州等沿海一带的西方异国人士都常常被冠以波斯之名。从这些方面来看,显然波斯胡人已经成为唐代西域胡人的象征及代表。其次波斯人鉴宝能力及医药文化的广泛影响。虽然唐代长安寄养着波斯流亡王子及其随从,不过唐代波斯胡人留下的更多印象是他们的经商能力及高明的医药技术,这在上面论述中多有反映。虽然唐代社会粟特商人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波斯商胡,不过提到胡人买宝鉴宝故事,则多指波斯胡人,如笔记小说记载他们往往能慧眼识宝,为求宝物不惜重金;即便垂死之际,也要将自己视若生命的宝贝传给后人。可以说在唐人眼里,波斯胡人是怀有宝物,善于鉴宝识宝的富商大贾。因而有学者指出,粟特人在识宝方面还是较波斯人逊一筹。[61]至于医药医术,则更是波斯人的专利,如前述李绚及其弟李玹,还有穆昭嗣等,都是因擅长医药之术而闻名,可以说经商才能及医药技术已成为中古入华波斯胡人的文化特征。波斯人对三夷教传播的影响。唐代随着西域胡人的大量入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传播进来,这就是唐代社会曾流行过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即三夷教。虽然学界倾向认为当时来华的三夷教徒多为粟特人,但是也不能否认波斯胡人在传播这些宗教上面所起的作用。波斯地区的正统国教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为祆教,因而来华波斯人应有不少祆教徒,前述苏谅妻马氏就是一个代表,从其双语墓志可以看出,在唐咸通年间,萨珊波斯的移民还仍旧保持自己传统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婆罗钵文字,可以说这个宗教在波斯人中影响很深。还有景教,也即聂斯脱利教,波斯地区是这个教派的大本营。据《景教碑》载: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中国称为景教,太宗其后允许其传教,在长安以宁坊设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又应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请,在醴泉坊设波斯胡寺,也即大秦寺。唐代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对景教表示好感,景教徒也曾公开在汉人间传教。特别是在“安史之乱”时,景教徒伊斯曾效力于郭子仪的朔方军中,“效节于丹廷,策名于王帐”,使得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作为奖励,可以说唐代景教发展更多是由波斯人来维持。至于波斯人在传播摩尼教方面,史载不详。摩尼教本身是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后被萨珊波斯斥为异端而遭禁断,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四散逃亡,向东传入中亚、中国的西域和中原地区。史载武后延载元年(694),有“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62]虽然学界认为唐朝流行的摩尼教更多来自中亚摩尼教团,[63]有更多中亚粟特人参与其中,但从拂多诞传教一事来看,也不能否认波斯人等的影响。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主要是用古突厥语和三种著名中古伊朗语即中古波斯文、婆罗钵文和粟特文写成,[64]其中中古波斯文、婆罗钵文本身属于西伊朗语,多少也可以提供相关佐证。因而在唐代三夷教传播上,波斯人更多地起到保持与维护的作用,在唐人心目中,他们更具有代表性。总之,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文明大国,波斯及其文化影响也随着波斯人东来波及到东方中国,这在唐代达到一个高潮。虽然在人数及文化传播上,他们比不上活跃在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但在泛海经商上,他们更有优势;在鉴宝识宝及医药技术上,他们更具有代表性;在宗教传播上,他们也更多地寻求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因而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作为西国胡人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影响不可忽视,。[1]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第5—76页。后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80页;张广达:《唐代长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各方面的活动》,唐代史研究会编《唐代史研究》第6号,2003年,第3—16页,后收入氏著《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68页。[2]《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页。[3]《周书》卷50《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20页。[4]韩香:《两汉迄五代中亚胡人的来华及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5]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1期,第14—16页及图版;钱伯泉《“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80—81页。[6](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7]《隋书》卷83《西域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1页。[8]《隋书》卷83《西域传》“安国条”,第1849页。[9]《隋书》卷83《西域传》“波斯”条,第1857页。[10][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5—516页。[11]《资治通鉴》卷180,隋大业三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635页。[12]《隋书》卷83《西域传序》,第1841页。[13]《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9页。[14]《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第6259页;《旧唐书》卷198《西戎传》,5312—5313页。[15]统计数据参见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16](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一)卷10,“醴泉坊”条,(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五十九年,第239页。[17]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16页。[18]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8—199页。[19]《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卷975“褒异第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50、11453页。[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壁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考古》1964年10期;[日]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壁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2期;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21].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第79页;参见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北大出版社,1998年,第82—83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9—244页。[22]见《大唐故陇西郡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87页。[23]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55—256页。[24]《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9页上栏。[25]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78页。[26]《阿罗憾墓志》,《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与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95—96页。[27]马小鹤:《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见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3—574页。[28]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31页;马小鹤:《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亦提出此观点,见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第553页。[29]《旧唐书》卷17上《敬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页。[30](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康老子”,《钦定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98页[3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32](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中华书局,2002年,第227页。[3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78—79页。[34]《北史》卷82《何妥传》记为“细脚胡”,中华书局,1974年,第2753页。[35]《隋书》卷68《何稠传》,第1596页。[36](清)彭遵泗:《蜀故》卷17“著作”条,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84下页。参引姚崇新:《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07—308页。[37](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条,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子部·小说家类》,商务印书馆,第887页上。[38]姚崇新:《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第308页。[39](宋)路振:《九国志》卷七《后蜀志·石处温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史部·别史类》,第307—308页。[40](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22《晋巴东怀濬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62—563页。[41]《太平广记》卷98《怀浚》,第656页。[42]《全唐诗》卷230杜甫《解闷十二首》,中华书局,1992年,第2517页。[43]《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第3537页。[44]郑阳、陈德勇:《扬州新发现唐代波斯人墓碑意义初探》,《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3期,第60页。[45]《太平广记》卷402《李勉》,第3240页。[46]《太平广记》卷17《卢李二生》,第119页。[47]荣新江:《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域南方的粟特人》,载韩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48](唐)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49][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50]《太平广记》卷34《崔炜》,第216—220页。[5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1-286页。[52]朱雷:《跋敦煌所出《—兼论“勋告”制度渊源》,载氏著《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53]《太平广记》卷402“径寸珠”条,第3237页。[54]《太平广记》卷403“紫末羯”条,第3251页。[55]《太平广记》卷402“李灌”条,第3240—3241页。[56]《太平广记》卷404“岑氏”条,第3261页。[57](宋)赜藏主编:《古尊宿语录》卷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上栏。[58]蔡鸿生:《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59](清)吴兰修撰,王甫校注:《南汉纪》征引《清异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7页。[60](南宋)庄绰:《鸡肋篇》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61]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78页。[62](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39,原著一说为“西海大秦国人”,即今叙利亚一带,《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369—370页。[63]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页。[64]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