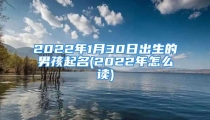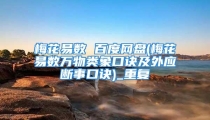广州10岁女孩潘晓谊,盼望能站起来。10个月大时,她被确诊患有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简称SMA)。每长大一天,身体就更衰弱一点,被困守在一张轮椅中。2019年2月,全球首个治疗SMA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我国成功上市,定价近70万一针。今年春节期间,晓谊和许多病友用上了曾经难以触及的“天价药”,仅在医保报销后,一针降到了1.1万元。2月15日元宵节,晓谊在医院度过。前几天打完针后,她就被送去做康复治疗。令家人欣喜的是,她的上肢力量有了变化,“量表评估,分数有一点点进步”。去年12月3日,国家医保局宣布,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许多SMA患者的命运从这一天转变。晓谊等待注射诺西那生钠。“一针成功”2月9日上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注射。那支装着5毫升液体的小药瓶到达病房前,所有人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遗传内分泌科主任刘丽召集了多学科专家会诊,小患者潘晓谊算着打针的时间,刚从上一场肺部感染中康复。父亲潘庆雄扒在门外望着,想到未知的痛苦,心里发紧无所适从。9时许,药到了,装在蓝色冷藏保温箱里。它看似与普通疫苗无异,但名字决定了它的特别——诺西那生钠,一种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即SMA)的特效药。医生取出握在手中,用体温一点点回暖,测温枪扫过,25℃,正是合适的温度。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一瓶5毫升,近70万一针,进医保报销后1.1万一针。晓谊侧躺在床上,从背面看,她的身体呈现“C”字型,脊柱已严重侧弯扭曲,腰间露出一小块皮肤。这一针要刺入脊柱椎间隙,脊柱变形为注射带来难度。医生们反复研判,寻找合适的进入角度。晓谊身子蜷缩着,两只手使不上劲,费力地攥紧,眼神里流露出惊恐。一名护士走过去,握着她的手,一直在身旁安抚。药瓶里的液体被抽得一滴不剩,珍贵的液体沿着一根长长的针管,被缓缓推入腰椎间蛛网膜下腔。从穿刺到注射,全程不到15分钟。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一针成功!”晓谊今年10岁,是一名SMA患儿。这个春节前后,许多病友在新年的期盼和热望中,用上了曾经难以触及的“天价药”。刘丽所在的医院忙了起来,她告诉南都记者,“将近40多个SMA新患儿准备打第一针”。她和同事筹备了工作组和治疗场所,接受患者预约、评估,并安排打针时间。晓谊曾经能独坐,有着藕节般的小腿,脸蛋胖乎乎。后来一切都在消退,全身肌肉逐渐萎缩,摸上去只有骨头,四肢无法动弹,被困守在一张轮椅中。8个月大时,她发过一场高烧,退烧后身体变得软软的,抬头翻身也不再灵活。潘庆雄在亲友提醒下,带孩子到医院。几乎没有走弯路,2012年10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经过基因检测晓谊被确诊为SMA。报告出来时,她的双脚已不能动,无法自然抬起双手。SMA是一种因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1突变所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1/10000。按照严重程度,分为Ⅰ型、II型和Ⅲ型等,最严重的Ⅰ型患儿,常因呼吸衰竭,活不过两岁。普通人群里,约每40至50人中,就有1个是SMA致病基因携带者。但绝大多数人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这一切,作为一种罕见病,它尚未被纳入常规孕检或婚检中。“这个病没得治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告诉潘庆雄。像所有初次确诊的患儿家长一样,他有些发懵。他只听过癌症是世上的绝症,这种陌生的疾病会将孩子带到何处?随着病程发展,先是不能站立行走,然后吞咽变得困难,呼吸功能不全,饱受肺炎等疾病困扰,直至生命消逝。晓谊是II型SMA患儿,潘庆雄向南都记者回忆,在医学词典上看到这些,“眼泪在流,手都是抖的。”那时,全球都没有治疗方法,按照脑瘫对症用药,也只是徒然的尝试。他带女儿寻找偏方,吃野生青蛙,做特殊理疗,跑了很多地方,也上当受骗过。这是所有SMA患者面临的境况,不得不接受现实,他们的病无药可治。确诊那天,潘庆雄给影楼打电话,预订了10年的全家福,“人齐的时候,有一年拍一年。”呼唤药物晓谊活着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疾病缠斗。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医院,最好的朋友是年龄相仿的病友。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各类并发症不时袭来。有三年的时间,潘庆雄一家几乎“住”在医院,最多离开半个月,又会因为肺部感染等,跑回来看病住院。对常人而言的普通病症,在SMA患儿身上,却是致命打击。两岁那年,晓谊正在医院做雾化治疗,毫无预兆地呼吸急促,越来越喘。身上连接的监护仪器开始报警,血氧、心跳、脉搏,远在正常值之外。医生当场宣布,送入ICU抢救。历经18个日夜,撤掉呼吸机,命救了回来。家里至今还保留着每次被送入ICU抢救时,晓谊佩戴的手环、亲人的探视卡,和搜罗的各种药瓶、药盒。潘庆雄觉得,那是他“最黑暗的三年”。病房里有一扇窄窄的窗子,上午阳光扫射进来,他“好像看不见”,“永远背着光生活。”每天时间过得飞快,盯着打针换药、擦身翻身、拍背吸痰、喂奶护理,几乎无法离开病床,要跑着去上厕所,来不及出去吃饭。到了晚上,就在女儿病床下铺张垫子,躺下凑合睡一夜。晓谊与外界的唯一连接是手机里的病友,有一位小一岁的Ⅲ型SMA患儿,她尚且能站起来,但也常在医院。她们缺失了正常孩子所拥有的大部分童年生活,小小的世界被疾病装满,总是在微信上问对方,“什么时候出院?”潘庆雄和女儿潘晓谊。潘庆雄仍在努力寻找有关SMA的治疗信息,他四处发邮件、打电话,发动国外同学联络资源,辗转找到了国内最早的患者论坛“SMA之家”。论坛的创办者马斌,患有Ⅲ型SMA,今年49岁。马斌向南都记者回忆,4岁时,他开始出现走路不稳的症状。高一那年冬天,行走退步得厉害,上楼梯已十分艰难。和陌生同学在一起,他感到孤独彷徨,选择了退学,坐上了轮椅。马斌父亲是昆明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退学后家人带着他四处求医。直到1993年,在北京301医院,得到了确诊结果。那时,中文世界里关于SMA的信息几乎一片空白,马斌利用所学的英文查找资料,不断学习有关SMA的研究知识、护理方法。世纪之交,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2002年,他把翻译的资料、最新的资讯,通过网络传递给病友,搭建了“SMA之家”。在无边的迷茫和“黑暗”中,这里是一盏微弱的灯火,足以给人们温暖,使人们聚集。2012年,潘庆雄结识了马斌,在电话里聊了许久,“启发很大”。马斌欣慰地看到,因为及时获取科学信息,有患儿家长少走了弯路。但他也体尝过无奈,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患儿家长,依然会传来孩子离世的噩耗。“SMA之家”专门开辟了一个板块——“百合山谷”,为了“纪念那些曾如夏花般绚烂的SMA小小斗士”。一位父亲在清晨时分写下,前一晚在火车上手机没电了,无法分散精力时,女儿生前的点滴,又在眼前出现了。他永远记得,临别前,女儿紧紧握着他的手,望着他。孩子离开快两年了,他想“在梦里见见”。一位母亲刚休完产假,孩子不在了。上班第一天,她又想起“小宝”,“在天堂做个快乐的天使”。潘庆雄曾亲眼目睹生命消逝,他加入的SMA病友群里,“走的孩子,每个月都有。”这些心碎都曾真实地存在过。论坛建立以来,最主流的声音,就是持续不断地对药物研发的呼唤。争取“活着”所有病友中,最特殊的一位叫“美儿”。她来自四川成都,2012年5月出生后,被确诊为Ⅰ型SMA,17个月大告别人世,没有用过一粒药。美儿的母亲冯家妹,在川渝地区为人熟知,她曾参加过“超级女声”,与李宇春等人闯进成都四强。美儿离开那天,家里飞来了一只蝴蝶,落在她手上,久久未去。她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接受这一切,在微博里坦陈遭遇,重新振作。更多的SMA家庭找到她,向她倾诉求助。“他们的家庭正在重复与我一样的苦难。”冯家妹有了新的想法,在为美儿奔波治疗时,她认识了马斌。2016年1月,两人共同发起注册了国内首家专注SMA领域的公益组织,以女儿的名字命名——美儿SMA关爱中心。三个月后,开始收集信息建立患者数据库,推动疾病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人类试图战胜罕见病SMA,从发现疾病之初,全球科学家接力,寻找治疗靶点。在“SMA之家”,国内外在研新药的动态和讨论随处可见。诺西那生钠I期临床试验启动的消息,至今仍是阅读量最高的帖子。“不但安全且耐受良好”,“在干预疾病进程方面表现出明显改善”,这些话语振奋人心。2016年圣诞节前夕,诺西那生钠在美国获批上市,是全球首个治疗SMA的药物。这是献给人类的礼物,却也是昂贵的礼物。一针12.5万美元,前两个月注射4针,此后每四个月1针,年年如此,终身用药。“无能为力。”价格出来后,潘庆雄不敢再想,绝大多数家庭都望尘莫及。每长大一天,晓谊就更衰弱一点,争取活着的时间,等待降价、新药出现,成为父女俩最大的动力。晓谊的家里被改造成了小型“ICU”,床边摆放着咳痰机、无创呼吸机、雾化器、空气净化器,四周缠绕着大小粗细不一的管子。她躺在床上,身下是医院ICU同款的护理床垫,由于不能自主移动,20分钟要翻一次身。常人轻松完成的呼吸,也要靠机器彻夜辅助。晓谊在家里做雾化治疗。入睡前,戴上鼻面罩,机器配合自主呼吸,输送丰富的氧气,肺部微微张开,负压抽出二氧化碳,脆弱的呼吸肌得以充分休息。早上醒来,雾化器开始嗡嗡作响,变成雾状的药液,顺着一根细管,缓缓进入鼻腔。为了维持活着的基础——顺利呼吸,如此日夜循环。房间里,唯一的童真气息,是几只乌龟玩偶,放在晓谊身边。她最喜欢乌龟,家里也养了一只。玩偶们被她命名“姐姐”和“弟弟”,晓谊还有个弟弟,患有自闭症。爸爸说,女儿就像是“小乌龟”。“坐”起来时,晓谊要从头到脚“武装”,穿上定制的马甲护具,前胸后背被紧紧包裹,像一身坚硬的盔甲,支撑起无力的脊椎。四肢被套上矫形器,脖子里戴着颈圈,因为长期躺卧不便,她没有留过长发,与纤细的身体相比,头显得格外大。“好像很怪一样。”潘庆雄望着女儿,笑着说。他从不避讳在晓谊面前谈论疾病,SMA患儿心智与常人无异,两三岁以后,晓谊发觉了自己的不同,拒绝别人说起病情。潘庆雄告诉女儿,“你只是不能站起来。”他给女儿看霍金的视频,告诉她就像这样,这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跟她讲国外的一款辅助设备,如果有一天能用上药,可以穿上它站立行走,看起来就像铁甲威龙、钢铁侠。他尽量不让疾病的阴影笼罩在家庭之上,晓谊和弟弟生病后,他关掉了公司,专心照顾女儿,妻子则带大弟弟。曾经家里唯一的收入,靠他晚上出去开网约车。日子虽有些苦,但也苦中有乐。比如驱车1200多公里去参加一场难忘的病友生日会,推着全副“武装”坐在轮椅上的女儿到公园嬉闹,或是把她从床上抱起,到南向客厅里安享冬日的太阳。时光,在这个家里安静地流淌。渴望“正常”晓谊6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她的残疾证上,等级是最严重的一级,意味着肢体重度伤残。那时,潘庆雄听其他父母说,因为身体脆弱、无法自理,SMA患儿入读公立学校,常常被拒。他希望孩子拥有正常人的教育,想去试一试,又有些担心。2018年5月的一天,他推着晓谊来到户籍对应的沙河小学。校长郭淑珺就在校门前,潘庆雄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他强调,孩子的安全自己负责,他可以全程陪读,甚至自备桌椅,只求一间课室。郭淑珺完整听完,没有犹豫,肯定地说,“只要孩子身体允许,我们无条件接收,做好上学的准备。”唯有说到这里,潘庆雄眼圈泛红,哽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顺利,确实很感动。”也许疾病不会摧毁人的意志,但善意能使人心柔软。回想起那天,郭淑珺觉得那只是一个平常的决定。“国家义务教育,应该接收。”她告诉南都记者,在她曾经任职的另一所小学里,一名三年级的小男孩也患有罕见病,她曾亲眼目睹,一场感冒夺去了孩子的性命。“我们是幸运的普通人,对于不幸的他们,在有生之年,要尽力去帮。”教学楼一楼是架空层,晓谊的课室被安排在二楼,离卫生间、楼梯最近,方便轮椅出行。每天,班主任兼英语老师黄晓路从楼下经过,看到停放的轮椅,就知道晓谊来了。潘庆雄请工人给女儿做了特制的木椅,比普通椅子占地更大,父女俩坐在最后一排。黄晓路不想让晓谊“有被忽略的感觉”,英语课上会主动递上麦克风,请她回答问题。爸爸是晓谊的“同桌”,帮她翻书、举手,抱着她站起来,和老师对话。全班一起朗读课文时,潘庆雄的声音总是最大。更多的时候,晓谊“坐”不了太久,要躺在放被子的柜子上,侧着看黑板听讲。最开始,班上也有同学好奇,下课后围过来,问她,“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原来的班主任崔璨在背后做了些工作,趁晓谊不在时,她教孩子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包容。潘庆雄想让女儿知道,“你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晓谊也会换上礼服,被爸爸抱在怀里,准时出现。每月一次的消防演习中,操场上都有她和同学集合、撤退的身影。有时外出参加集体研学活动,大家会预备些零食吃,小朋友们总爱拿给晓谊,回来后,爸爸发现,带回的零食比带出去的还多。原本,孩子们每升一个年级,课室就要统一向楼上搬迁。但是,晓谊和她所在年级的课室,整整三年,都没有动过。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被转到另一栋教学楼更大的课室,也在最低的二楼。老师们都觉得,除了身体不方便,晓谊和其他同学“差不多”,“努力,坚强,阳光,开朗。”晓谊也喜欢上学,但上学,并不容易。疾病在侵蚀每一寸身体,双手严重变形,只能用两根手指夹着笔,缓慢地写字。“她写1个字,别人可以写5个字。”崔璨带了她四年课,还记得,以前晓谊左右手换着写字,可以独立完成语文试卷,在班级里成绩优异。后来手部力量减退,不能再应付一场考试。身体的退化肉眼可见,长到10岁,晓谊也只有34斤。吞咽功能严重下降,一顿饭要吃四个小时,只有上午能去上学。等来“礼物”潘庆雄总担心,哪一天意外会来。2019年5月,晓谊再次被送进ICU抢救,这次,离死亡最近。在医院看病留观时,女儿突然叫了一声“爸爸”,再也发不出声音,舌头外翻,几乎窒息。来不及按铃等应答,潘庆雄抱着孩子直接冲进抢救室,医生迅速进行气管插管。因为腺病毒感染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晓谊在ICU呆了近一个月。当年2月,渤健公司研发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过优先审评审批,在我国成功上市,定价近70万一针。根据渤健在中国的援助方案,最初的四针“买一赠三”,之后变成“买一赠一”;第一年需要自费140万,之后每年平均花费105万。潘庆雄动了卖房打针的念头,但面临终身用药,也难以为继。身边的亲人、病友,沙河小学,为晓谊筹了款,老师们来医院探望她,带上了乌龟玩偶和一本“小册子”,里面是同学们写下的祝福话语。一位三年级的小朋友说,“晓谊,如果你卖了房子,那你以后还住什么?所以,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治疗,你一定要战胜病毒,早日归校。”那段时间,马斌也和潘庆雄保持联系,商讨如何用药。当时,另一款治疗SMA的基因药物在国外即将上市,只需一次用药,可以长期缓解,甚至治愈疾病。潘庆雄决定再等一等,寄望能用上这种药,即使倾家荡产。刘丽从医30多年了,担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组成员、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主任委员。2019年,她所在的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被遴选为广东省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省级牵头医院,是当地诊断罕见病最多的医院之一。她见过许多SMA患儿,“这种孩子很可爱,求生欲望很强,会积极配合治疗,很听话,因为他们想活下去。”刘丽记得,诺西那生钠在国内刚上市的前两年,她所在的医院“只有四五个人打针。”听到有药可治,大家都高兴,但知道药价后,又退却了,“父母不忍心放弃治疗,他们是很自责的。”后来,渤建调整援助方案,最低时,平均每年需要花费55万。这仍然是一个难以承担的数字。“70万一针天价药”,“众筹打针”,这样的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没有药没办法,现在有药了,我们就得想办法。”刘丽说。如何让诺西那生钠抵达患者,在不同场合,被反复探讨。“最后一公里”,是一步步推进的。全国多个省市,开始探索商业补充医疗保险。2020年前后,广东佛山、广州先后推出“平安佛”、“穗岁康”,诺西那生钠等罕见病高值药物,被纳入保障范围。后者赔付比例为70%,也就是说,原来第一年自费的140万,可以报销96万。刘丽欣慰地看到,这一年后,打针的人“又多了十来个。”但被寄予最大厚望的,是国家医保谈判。去年12月3日上午,SMA病友群里突然消息刷屏——“诺西那生钠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3.3万元一针!”潘庆雄和女儿正在学校上课,“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就是情不自禁,这个价钱想都没想过。”美儿SMA关爱中心向南都记者表示,听到“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很多家长都瞬间泪奔,从心底里感谢国家。”2月9日,潘庆雄打开那张医院清单,仅在医保报销后,一针降到了1.1万元。“现在大家都轻松了,没有人再谈钱。”第二天,晓谊出院后,又被送去做康复治疗,元宵节也在医院度过。令人欣喜的是,她的上肢力量有了变化,“量表评估,分数有一点点进步。”转眼,第十年了,今年的全家福拍摄,换成了一场生日会。宣布诺西那生钠进医保消息后的第三天,晓谊度过了10岁生日,爸爸说,这是她最好的“生日礼物”。那天,她许下心愿,未来,还能站起来。过去那些年拍的全家福,挂满客厅和卧室,色调是那样明亮。一家人整整齐齐,脸上洋溢着喜悦,好像没经历过这一切。出品:南都即时采写:南都记者张林菲实习生崔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