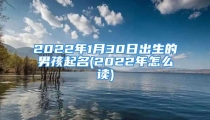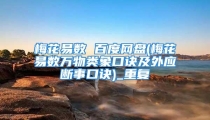1959年春节后,袁克夫正式踏入社会,那一年他不满十四岁。
在1958年冬,哈尔滨电影院举办印度电影周,其中一部“流浪者”给袁克夫留下深刻印象。小偷“拉兹”被演绎的潇洒又充满正义,尤其是赢得美女丽达的真挚爱情,那个能歌善舞的印度美女真是漂亮啊。大银幕上人物性格的演绎表现力量是无法想象的,银幕上人物的形为说服力宣传力都能让当时的人们绝对信以为真,很容易就为人们树立起模仿的榜样。偷窃手艺高超的流浪者拉兹,成了当时袁克夫和一批哈尔滨青少年的崇拜对象。
道外的市井百态,浓郁的民间烟火气息深深的符合袁克夫的口味。在那没有眉头深锁和正襟危坐,人们虽然贫穷却乐观,在整体严肃压抑的大环境下,道外的人却总能坚持自由和开朗。在道外,袁克夫交了很多朋友。只要他兜里有钱,就绝不吝惜的请哪怕再多的朋友喝酒吃饭看戏,这些也是当年的头等大事。道外的许多人也喜欢这个带有浓烈山东口音豪爽直率的小孩,义气相投,兄弟至上。那个时期,很少有人虚头巴脑,或借点名气牛逼哄哄趾高气昂,大家都想在贫困的生活中寻求点快乐,增添几分色彩。一次,袁克夫整到了六七元钱,和升平街黄德福,草市街方玉山等几个人在桃花巷“老边饺子馆”吃饭,袁克夫点的熘肉段,凉菜,红肠小肚拼盘,尖椒干豆腐和一盘饺子。要这么点菜,就想让那几个好喝的多喝几个两毛钱一罐头瓶子的啤酒。这时,碰到了四道街的封大权,三十岁的封大权已是道外社会圈颇有名气的“老人儿”了,几个人纷纷打招呼让座,小孩儿袁克夫有点尴尬,平日“大权”没少照顾自己,今天菜这么少,兜里钱还不太宽裕。“大权”根本没当回事,连连拍着袁克夫说,你们喝酒也不叫大哥一声,大哥自罚三杯。说毕,连干了三罐头瓶子啤酒。喧闹中,大权暗中买了十罐头瓶子啤酒,化解了袁克夫的尴尬。
袁克夫喜欢道外的人情味,喜欢那毫不做作的嬉笑怒骂,也喜欢那的精明市侩。在学校门口的宣化街上,等来“3路”大气,坐到终点就是道外桃花巷,穿过“五柳街”,“天一街”和“延爽街”夹着形成的裤裆街,在穿过“靖宇街”,就是北三道街,那里热闹非凡,还有一个“省评”黑龙江省评剧院,每当演戏时人山人海,最开始袁克夫就在那“下手”。那阵的人都喜欢用钱包,塑料制成,几角几分钱也放到钱包里。没拜过师没受过“串”的袁克夫就凭胆大心细的愣干,但常在河边走,必有鞋湿时,虽然塑料外皮的钱包滑溜好“拿”,但得手几次后的袁克夫还是“响”了,被大队便衣“拿”住,扭送到设在“桃花巷”市局大队的一个点。
1959年,东,西傅家合并,称作道外区还不到三年。原来的两个执法队合起来称作道外区公安分局,统一隶属于市局管理。市局鉴于道外治安难度很大,当地警民关系过于“密切”,执法手段不够严厉,便从市局抽调精干人员和特聘的旧时期经验丰富的特情人员组成一个队伍专门在道外最繁华的桃花巷设立了一个办公地点,加强道外的治安管理力度。
这个大队确实厉害,又六亲不认,许多当地的賊纷纷落网。当穿便衣的他们,出现在哪,凭他们那几张熟悉的脸就对那个地方形成震慑。初出茅庐的袁克夫却不认识,当然是被手到擒来。黄铜铐子的一头铐在屋里的一张破木床的床头,另一头铐在右手上的袁克夫蹲在床头旁边,他的脑袋旁边,一双三接头皮鞋随着床那边半导体播放着哼哼呀呀的京剧有节奏的晃动。他心想,这种皮鞋可能都是市局统一发的,这一次可能得去道外看守所了。
屋里挺大,中间炉子上的大铝壶冒着腾腾热气。三四个人走来走去显得挺忙,两个人在一个破桌子上下棋,棋子被摔的啪啪作响。小山东儿袁克夫环视屋内,没人打理他,有过一次拘留所的经历,此刻他没想那么多在道外看守所是啥样,和这次回到家又会是啥样,他想的最多的就是抓他那一瞬,自己的姿势丢不丢人,他回想起来看热闹的人堆儿里,南十道街的藤浦,良子,线黄瓜等道上的“名人”都挤在里面,还有几个大姑娘小媳妇也挺漂亮的,自己被扭起来的姿势不算难看,言行不丢人,甚至还有几分电影里昂首挺胸的英雄人物的样子。想到这,他觉得自己已经和无名小卒划清了界限。想得美了加上蹲的腿麻,顺势就坐到了地上。这一坐,他那庞大的身躯就带动了那张破床晃动了一下,黄铜铐子一紧,勒的袁克夫诶呦的叫了一声。
“干他么什么呢!”一个嘶哑的声音响起,随后从破床上弹起一个人。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脸上皱纹如同刀劈斧凿般深刻进去,稀疏的头发下一双小眼精光四射。
“谁让你坐下了。”瘦子抡起瘦腿,一脚踢在袁克夫后背上。
“肚子痛,肚子疼的受不了了大哥。”袁克夫重新蹲了起来。
“你个小崽子给我叫大哥?”黑瘦子坐到床头,居高临下看着袁克夫说“咋地,中午好东西吃多了?”
“没有,没有”袁克夫不知啥意思,没法回答。
瘦子搁兜里掏出盒烟,拿出一根,在床头墩了两下,让烟丝更紧密点。点着,狠吸了一大口,喷出烟雾后问,你掖县哪的?
“俺西由的。”袁克夫一看这人直接听出自己口音是掖县的,心想可能是老乡,就彻底放开说老家的话了。
“挺大的个子,不学好,大老远跑这干这个事”瘦子一口标准的哈尔滨普通话。
“俺在哈尔滨上学,为了交学校的三块钱杂费,俺这也是第一次。”袁克夫认定讲掖县话能给对方带来好感。
“他娘的”瘦子顺手给了袁克夫一撇子,袁克夫那诚恳的目光和一口朴实憨厚的山东话并没让这个人轻信,“你一个掖县农村小孩,咋能上这来上学,你哪个学校的?”
回答这个问题,是袁克夫的强项。
他如实的述说小时候的悲惨命运,父亲的早逝,母亲艰难困苦的生活,无奈的过继到现在的伯父家,伯父酗酒后的打骂体罚,十三中老师同学如何瞧不起一个农村小孩,说到动情处,自己也是泪流满面。他还提到伯父早先也是东傅家执法队的一员,因为是文盲,才调到银行保卫科,以此来暗示瘦子看在曾经同僚的份上网开一面。
这段大部分是真实的叙述似乎让这个目露精光的瘦子相信了。喊了一声屋里的一个高个子,接过了高个子抛过来的一串钥匙,一边给袁克夫打开铐子,一边说,小孩,你知道你偷的钱包里有多钱么。
袁克夫不语。
“就几分钱”瘦子打开手铐“手里拎着刚买完菜的娘们,钱包里有几分钱就不错了”。瘦子把解开的黄铜铐子抖弄一下,扔床上,说,这玩意儿你心思谁都能配得上戴着啊,回家吧小子。
小山东袁克夫如释重负,朝瘦子深鞠一躬,然后故作镇静缓步离开。出了那间屋子大门,加快脚步,向车站奔去,心想,今天侥幸躲过一劫。
当天晚上,他仔细回想在市大队驻道外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些人,把那些人脸部特征,身高体型牢牢记住。以后在人堆里行窃,得防备那几个人。摸荷包这个事不管怎么样都得继续下去,目前没有别的路。
第二天,袁克夫在“北三省评”转了一圈,他看到平日里常盘踞在那的几个賊看到自己被抓第二天就露面,都有惊讶的神色,袁克夫故意露了一面,目的达到后挺得意,转身去往靖宇街。在靖宇街转悠一个上午,十点多钟,在竹林商场有了收获,“拿”了一个中年干部模样装在裤兜里的一卷钱。拐到“恒发祥”对面的旱厕里一数,有九块多钱和六斤粮票,很是高兴。把钱放好,刚出了胡同,就看到俩二十多岁的青年斜眼看着自己,这眼神不像是友善的目光。袁克夫感觉这俩人绝不是“大队”里的人物,凭经验,他俩也就是一种学校周边常见的地痞混混一类的,想要见缝插针瞄着自己,而自己一旦示弱,那就永远别想脱离他们的欺压了。想到这,袁克夫伸了一个懒腰,顺手做了几个扩胸运动,在那俩人面前吹着口哨,目不斜视泰然自若的走过。
有可能是袁克夫不符年龄的高大魁梧,暂时震慑了那两个人。重新拐到靖宇街上的袁克夫在人流缝隙中快速回了一下头,看到俩人变成了四个,亦步亦趋的还缠在后面。他走到一家五金店门口,在门口的柴绊子堆里,随手掏出一根手臂粗细的木绊子,拿在手中,用力的往旁边的树上砸了一下,好像在实验这跟棒子的坚硬程度。他想好了,如果这几个人当街把他围上,他就用这跟棒子毫不犹豫地放手一搏。任何威胁他在道外有立足之地的事,他决不惜一切代价去争斗,因为当时他毫无退路可言。
柴火绊子在他手中上下抛动,他再也没有回头看那几个人。拼命决心一下的同时,脑子里电光火石般的生成一个想法。袁克夫的脚步跟随他刚产生的想法迈向桃花巷,他想,昨天那个市局大队便衣警察不知姓啥,瘦子放了他,今天有钱了,得表示一下谢意。从昨天瘦子跟自己说话的态度,不可能追究自己表达谢意所花钱的来源,再把自己抓起来。搏一搏吧,真要能完美的表示了谢意,也算在市大队里认识了人,认识了这样的人,以后还有啥不好办的。
在南头道街街口,袁克夫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一盒好烟,古巴出的细支雪茄烟扁盒的“红骆驼”。把烟揣兜里后,他就来到市大队在桃花巷那个红砖平房旁,把那根柴火绊子垫在屁股底下坐在那,环顾四周,人来人往,没再发现跟着自己的那几个人,于是盯紧大队那个铁皮门静等瘦子出现。
等了半天,近中午时,瘦子从门里晃了出来,缓步向前。袁克夫跟上,待瘦子拐到五柳街上,紧走几步,拉了那人衣袖。说,大叔,我给你买了一盒烟。说着把烟放倒那人手中。
瘦子拿烟看了看,打开,弹出一支,深吸一口,浓郁的烟雾从鼻子嘴里喷薄而出,说,学校交的钱整到了?烟雾没影响他说话。
“钱,交上了,昨天的事我就是想来谢谢你。”
“小孩儿挺懂事,还谢谢我。”瘦子一笑,脸上皱纹深凹进去。
袁克夫觉得那人脸上皱纹深处有着数不清的故事,好奇心起,又说,大叔,咱俩一起吃饭吧,到现在我还饿着呢。
“吃饭?你要吃啥饭?”
“啥都行,大叔,咱吃啥都行。”
“你小子,又没少整,看样。”瘦子背手前行,袁克夫跟在旁边。
从五柳街转到水晶街又穿过南五道街,又来到了靖宇街,一路上不少人和瘦子点头致意,看来这个瘦子在道外熟人很多。
在靖宇街上,瘦子进了一家回民饭店,饭店里人声嘈杂座无虚席。在那个火红朴素的年代,道外的人对吃还是格外重视。道外人市侩精明,分毫必争,但也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那时,很多蹬三轮,拉小套的在道外居住,挣的钱就是一天一花,某一天多挣了点就去割点肉打点酒,全家乐呵,那年代没有房子,医疗,教育的压力,挣多少花多少,绝大多的钱数贡献给了肚子,在这真正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跟着进来的袁克夫看见认识瘦子的服务员带领瘦子进入挂着写雅座白门帘里面,他就转头看那个供点菜的黑板。黑板上没写几样菜,他点了“溜羊肉片”,“炒干豆腐片”,“溜肚片”,“油炸花生米”,“羊杂碎汤”和“烧卖”,主要的是一瓶“德惠大曲”,他感觉瘦子是个好喝酒的人。这些花了将近六块钱,反正留着钱也没用,他转身出去,又买了一块钱猪头肉和一盒“红骆驼”。
“小子,这玩意不能在这吃。”瘦子一看袁克夫拿的猪头肉,一把夺了过来。
瘦子细嚼慢咽,仔细品尝菜肴,呷每一口酒都是很陶醉的样子。袁克夫竖起耳朵细听瘦子说的每一句话,这个人的每一句话都饱含丰富的知识至少是有用的信息。比如,回民饭店因为是少数民族,比汉族饭店要贵一些,但肉类供应要多一点,想吃香的,还得回民。还有就是,一条街一段路,一个商店或一个剧院都有一个似乎默契约定的XX人的地盘,等等。当天,两人相谈投机,全然不像是相差四十岁的样子。
这个瘦子,就是三四十年代,哈尔滨江湖中的知名人物,解放后被哈尔滨执法队即后期的公安局聘用当特情至今的陶喜斌。
陶喜斌爷爷那一辈就从山东莱州〈掖县〉来到东北,淘金,挖参,拓荒,到了父亲那代,家中以颇有资产。1907年,陶喜斌出生的前两年,陶家在傅家甸〈道外〉头道街靠江边船坞码头处盖有雕梁画栋的砖瓦房屋二十余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一场大火,房屋被烧成一片平地,所有财产尽归祝融氏。
1910年春,狂风在松花江两岸肆虐。许多贫苦人家的茅草屋顶,马架子,地窨子都被大风席卷而去。坐落在傅家甸北二道街青砖欧式门脸二层楼的娼窑“青云书馆”却岿然不动,灯火阑珊,众多妖娆的女人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迎来送往,热闹非凡。起名书馆,表明和普通的妓院不同,这里表面上是以听书听曲为主,女人们能说会唱,又都懂几分棋琴书画。评弹,大鼓,京剧的一技之长提升了这儿档次,以江,浙一带女子为主的“书馆”收费昂贵,普通人想来此春宵一渡那时绝对承受不起。彼时,“傅家甸”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充当俄国劳工捞到第一桶金的拿着钱从事各种生意,衣着光鲜的山东小伙随处可见。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山东人衣锦还乡对家乡眷恋的思想使他们抱着早晚要返回齐鲁大地的想法。有很多人在山东完婚后不带家眷独自回来继续在哈尔滨淘金,解决生理问题就成了难题。就这样,众多档次不同的妓院在取得当局的执照后,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许多俄国,中国的暗娼流莺也密布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北二道街的“青云书馆”调教了一些有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江南女子,从开业之初就标榜卖艺不卖身,有不可留宿的规定。来此都是高官财阀,军警要员,豪绅巨贾,实际就是属于最高档妓院。“青云书馆”,那些貌似清纯的“伶人先生”们在这些人一掷千金下,每夜都演绎着鸾凤之欢。
哈尔滨的春风强硬而又干燥,在毫无屏蔽的松花江两岸翻滚,春天,也让驻扎在铁路桥的俄国护路第七队的几个毛子兵春心荡漾。1910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喝的酩汀大醉的几个毛子兵终于压抑不住身心的饥渴向傅家甸方向而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北二道街的“青云书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