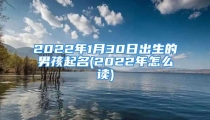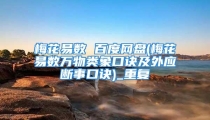作者:修文举
“象思维”作为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中广泛地存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意境”理论就根源于“象思维”。意境孕育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思想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
《周易》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由符号和文字组成的系统。它通过“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的“象思维”方式来判断吉凶悔吝。《周易》中的阴、阳两种基本符号以及由这两种符号组成的八卦和八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反映了我国先人化繁为简的能力和对世界、自然的深刻认知。“象思维”是与西方的“概念性思维”大为不同的诗意而灵动的思维方式,是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一书中指出,“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最终把世界设想为我们直接经验中所揭示的那种活动”。《周易》的“象思维”正是通过对人类自身、社会和自然界的类比思维而得出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也以整体性、动态性、生成性、非实体性和自我调整性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的本原性思维的基础。因此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周易》出现之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才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
“象”首先是人们对纷纭复杂的自然和人类自身现象进行观察,进而模拟,然后高度抽象而形成的,故而这种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并非任意的,而是一种相似关系。在“观物取象”和 “象以尽意”两个命题中,“观”、“象”、“意”是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概念。“观”,本意为感性地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周易·系辞》上),即 “具象之观”,这也是观的基本含义。而中国古人从具体之观出发,然后通过对“观”的结果的抽象归纳,得出符合规律、“尽意”的“象”,进而“模拟”进入“拟物观象”的阶段,“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即对观到的“象”有一个模拟的过程,然后逐渐上升超越,获得抽象之观。最后进入到“玄”,即宇宙大道的境界之中 。
《周易》的“象”在三个方面与艺术形象相通。其一,“象”是感性具体的,“见乃谓之象”(《周易·系辞》上)。其二,《周易》的“象”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模拟和反映。其三,《周易》之“象”是“相杂”而成“文”之“象”,具有美的意义。因此,“象思维”作为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中广泛地存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意境”理论就根源于“象思维”。意境孕育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思想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魏晋时期,产生了“言意之辨”,以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主张言不尽意,提出“声无哀乐”的命题,认为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它的价值并非传统思想和情感。而王弼以《周易》的言(卦辞、爻辞)、象(卦象)、意(卦意、圣人之意)概念为基础,对言象意关系进行论证,认为言是用来明象的,象是意的显现,尽意的过程则是由意到象、由象到言的转化过程。将“立象以尽意”与庄子的“得意而忘言”一说相结合,构建起一个“言、象、意”系统。为了实现“尽意”的目的,必须基于“象”,而又要超越于“象”,“象”是产生美的根源,“观物取象”不是目的,而是“尽意”、“求意”的桥梁。另外,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物”并不是唯一的,它的含蓄性和模糊性就为意境美发生与创造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陈望衡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中指出,《周易》中的“象”,不管是卦象还是爻象,既是物质性的概念,又是功能性的概念,但主要还是功能性的概念。“象”的最大功能就是变化。“变”既是空间性的,表现为物体位置的变异;又是时间性的,表现为时光的线性流程。这就为从“象”到“意象”直至“意境”的阐发提供了前提。
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有力地深化了对审美观照的理解。美的外化是感性而具体的,但审美观照能够超越具体事物的限制,达到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加深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如宗炳的“澄怀味象”的提出,认为“澄怀”就是要涤除内心的纷繁执念,形成一种审美心胸,这样才能体味到自然之美,即宗炳所言:“山川能够成为贤者澄怀味象之象,贤者从山水之象得以与道相通”,使得精神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解放。而从意象到意境的转变,发生在中唐时期禅宗思想兴盛的背景下,出现了从“象”向更加主体的“情”的转变,从而实现了由“意象”到“意境”的蜕变,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情景交融”,主体的情与思被置于艺术创作的核心地位。从唐代的“韵味说”到宋代的“妙悟说”,再到清代的“神韵说”,直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都认为诗与艺术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具体体现在“以小见大”、“虚实相间”、“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特征之中。
“象思维”和“意境”集中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古人造园,善于利用各种“藏与隐”、“虚与实”的手法体现朦胧、深远、幽长的意境之美。郭熙在《林泉高致》中阐释了中国画创造意境的方法,如讲到:“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即若要山显得高,画山时要用“烟霞锁其腰”的手法,而若要水显得远,则用“掩映断其脉”的方式。这些手法在园林空间的构建中也彰显出来。如以石为实,水为虚;以近景为实,远景为虚;以墙为实,以影为虚。正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说:“处处邻虚,方方侧景。”这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刚柔相济的方法不仅扩展了园林的空间,还能使人达到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审美感受。
园林中也善用“障景”的手法达到意境之美。“障景”是空间中设置景物作为屏障,以达到“曲径通幽”或“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深远意境。而“障景”与“隐”这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概念相关,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中,他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即“隐”强调文章含蓄,意旨多重,令人流连,体现出古人在诗词创造和欣赏上,讲求含蓄婉约,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而在中国园林中,“障景”手法的运用,并在园林中体现出来的藏与露、隐与显的辩证关系,充分彰显了 “隐”这一概念的美学意义,同时也突出了它们与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林泉之隐”和无法抛却“尘世之恋”的复杂心态。因此,在园林选址时,既要环境清幽,民居无多,以阻隔世间繁华,形成一个自我颐养身心的隐秘空间;同时还要借城市之繁华,出行便利,这种身心之隐和环境之隐的“异质重构”,形成了人与景、情与景、身与心的充分交融,使得园林的意境之美得以充分体现。如宋朝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记载:园地“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
从上可见,中国园林的意境之美是从《周易》的“象思维”而来,并通过“意象”范畴转化而来。在造园的过程中,借用隐与显、藏与露、虚与实等手法,充分体现出主体和客体、情与景、自然和心灵、哲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使园林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这也体现出《周易》的“象思维”中“立象尽意”所希冀达到的物我一体的目的。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视觉形式研究:从形式本体到意义语境”(13BZX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