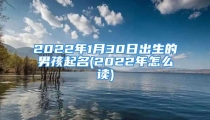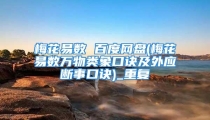我家的脱贫故事 ———父亲与奶牛 父母都是极能吃苦的人,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民中普通的两员。一如其他农村家庭,为了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父母在生涯中做了不少尝试,终变成了今日的“奶牛养殖专业户”。一、开荒种麦父母成家是在1979年。那个时候,土地属于金贵资产。祖父家七口人,登记在册的地也不过十亩。当时社会副业不畅,农户们并没有别的挣钱门道,生活自然清贫。结婚前的母亲家生活在兰州榆中县一个叫甘草店的小村子。受地形影响,当地农户普遍靠天吃饭:在山脚下或山坡较为平坦的地方点上庄稼的种子。若当年雨多,则庄稼收成好,雨少,则庄稼歉收。日子过得紧巴巴。上初中时偶尔问到过母亲:从靠近兰州的榆中,一路向西跨越900多公里来瓜州嫁给父亲的原因。母亲回答得很干脆:“你爸相亲时说了,瓜州是平原,地多能吃饱饭。再加上你爸当时坐火车吃剩的都是白面膜膜,我想那家里日子应该比我们这好。便同意举家搬迁来瓜州,落户在这儿”。结婚后分家出来的父母,不停歇的在队的西南角荒滩上开垦了40亩的荒地。逐一解决了挖水渠、除盐碱、换澄浆泥、挖砂层、垫肥土、拉粪补肥等问题后,他们的辛勤有了回报:地里的小麦丰收了。一眼望去,金灿灿的一片。清风吹来,麦浪滚滚。割麦是个大工程,那时瓜州还没有收割机等高科技。怕成熟的麦子被风吹落到地,母亲想了一个好法子:随黄随割。受土壤肥力等因素影响,同一块荒地上的麦子并不总是同时变黄。地力差一些的地方麦子常长得很矮、且麦黄的早。父母便先割了这些地方的。即使这样,等麦子大批量成熟时,两个人的手工割麦的速度还是远远跟不上的。母亲心小,晚上会睡不着觉,恨不得趁着夏日皎洁的月光连夜割麦。不几日,外婆与舅忙完了自家的麦子,便赶来帮忙。六七个人一排,每人占定一块地方,弓着腰,低着头,来不及聊天,“嚓嚓嚓”的割麦声在烈日下久久不息。打麦时,为了赶上有风的时段,大人们往往会提前观星查月、看天气预报、请好帮忙的亲朋邻居。风一来,大家便听风而动,十几个人碾麦、扬麦、堆麦、装麦,好不热闹。二、种棉花。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在瓜州流行开来。相较于麦子的浇水、除草、施肥等基本工序,棉花多了间苗、打头等。但棉花挣钱多。那段时间,棉农们买车、买楼房都不算是新闻。像大多数棉农一样,找摘棉工成了父母一年一度的心头大事。每年的八月底,棉花开始一小片一小片的开放。八月头,父亲便开始忙着给往年的摘棉工打电话,询问今年来不来摘花。或到斜对门的苏家预约陇西的摘棉工。如果以上两个途径都落空,去汽车站找人便成了不二的选择。每年到了棉花采摘季,汽车站便有大批的外地采摘工,来找采棉花的活儿。也会有更多的棉农,心急火撩的招采棉工,“抢人大战”时有发生。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采摘工的待遇也是水涨船高。除了每斤棉花采摘价由0.2元逐渐涨到每斤0.8元,报销往返的车费、每人赠送两床棉絮等条件也被陆陆续续提了出来,父亲对此怨声不小,却也无可奈何。若棉花开的实在太多,摘不过来。父亲也会想办法请本地的回族摘棉工来帮忙。因为宗教、饮食不同,请回族摘棉工,主家需为他们另备住房、灶头、米面、清油等。当然,一日三餐回族采棉工也会自做,不需要主家再出力。三、养奶牛。09年,我升入初中,家里也装了固定电话。嫁到玉门的三姑打来电话说,玉门奶牛场的一批牛,大大小小约20头,统一出低价处理。 问爸爸想不想养。几天后,我家200多平的后院,变成了奶牛的主场:追逐顶架、撒欢打滚。周五下午放假回家,穿过后院到前院的一段路,我总走得小心翼翼,连跑带躲,生怕被哪头牛盯上,用硕大的牛头砸我或顶我。卖掉不挤奶的小牛和公牛,扩好牛圈,父母的牛奶事业正式开张了。刚开始的订奶户,是住在城里的奶奶帮忙宣传和介绍的,而后客户逐步增多。奶票则是由做过教师的爷爷在烟盒裁剪的小纸片上一张一张写的,干净的小楷挺拔俊秀。父亲早晨、下午各送一趟。从四工一队一路向东,一斤、半斤的逐一将奶送到订奶户的门前。为了送奶,父亲买了队里的第一辆加油的三轮摩托车;为了储奶,家里甚至有了冰柜。父母是忙碌的:挤奶、送奶、喂牛、饮牛,还要照顾田里的庄稼。父母也是开心的,家里生活有了质的提高。卖完牛奶的父亲从县城返程,时常会带来各种吃食:冬天的大棚菜、秋天的桃李,以前一年中过节才能吃到的鸡鱼肉也几乎每月能吃到两三次。父亲每天看的书变了,由之前的《周公解梦》、《手相面相大全》换成了《养殖指南》、《饲料搭配》;父亲的关注点变了,由几十年不换的左亲右邻家的大事小情转到了当地养牛圈的最新动向。县里举行了几次赛牛大会,父母的牛拿到了二等奖、三等奖等名次。有时候还会得1000元,500元不等的奖金。给获奖者戴红花的环节,父亲总觉得不好意思,便推了哥哥上台去戴。养起牛来,父母越来越得心应手。遇到牛消化不好、感冒等,他们甚至能自己抓药,自己打针。零六年,家里的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变故。七头牛中有四头牛在一夜之间中毒而死。那时还没有奶牛保险之类的。父母只能自担损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常一起回想牛中毒那天的每个细节,想知道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却也毫无结果,只能不了了之。之后随着两人年岁的增大,便推掉了大多订奶户。只养着两头牛,供应自家人每日饮奶以及临近一些上门自取的订奶户。故事本应就此结束,然而这次似乎不符合父亲的风格。14年秋,应了几位订奶者的需求,父亲再次开始进城送奶。由于价格低且质量有保障,父亲的牛奶在经历了四个月的试卖后又变得畅销。奶牛由两头扩展到四头,再从六头到最多时的十一头。牛圈自然得扩大。政府有不少的相关优惠政策,比如圈砖的补贴,养殖无息贷款的发放等。随着瓜州经济的增长,县城的楼房变得多而高。65岁的父亲已做不到将鲜奶送到每家订奶户门口。他便只卖不定,每天固定的在阳光小区东门口摆摊。父亲对牛奶的纯度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一次利用傍晚闲暇时光,帮助父亲装奶。半斤、一斤用奶提子打好,一份份装入牛奶专用袋。装完半斤的,奶漏子上的纱网被奶泡糊住了。我便随手将纱网放到外边水龙头冲洗了一遍,转身准备继续装一斤的。坐在一旁吃晚饭的父亲急啦,坚持要求先把纱网上的水甩干,才能继续装奶。害怕我把把水滴带入鲜奶中。这方面,老头一直很倔。父亲的牛奶摊总是很热闹。除了卖奶,它还是老人们的“聊天据点”。最新的国家政策、政府惠民措施也常在老人们的讨论之列。他们的消息灵敏度常使得我惊讶。今年父亲已年近70,母亲也已60有余。两人的农村养老金已发放好几年了。每天两人依旧围着10头牛忙前忙后,除了睡觉,毫无其他放松时间。去年10月,父亲旧疾复发,气喘咳嗽。县医院检查说是肺部有些发炎要求住院7天并顺便做次全身体检。刚住够5天,身体好点的父亲便着急回家,心里总是挂念家里的牛。好在恢复确实不错,体检结果也显示身体状况佳,住院的费用更是由农村医保报掉了大部分。作为女儿,我更希望上了岁数的两人不养牛,安心养老。两人却总是各种理由推脱:舍不得长期相处的客户、怕养老的费用不够等等。结果是我与父母,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屋内装牛奶,一位临近的老人上门为半身偏瘫的老伴取奶补充营养。老人的年龄有父亲相仿,打奶已一年有余。等待装奶的过程中,我们谈起父母两人养牛的辛劳,我抱怨父母的固执:已近70的人了,该停下来休息了,不能再围着牛忙来忙去。老人却很理解父亲的做法,说这是他们辛劳了大半生铺就的摊子,是他们半辈子的事业,指定舍不得丢下。“半辈子的事业”这几个字顿时让我醍醐灌顶,一瞬间突然明白了父母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