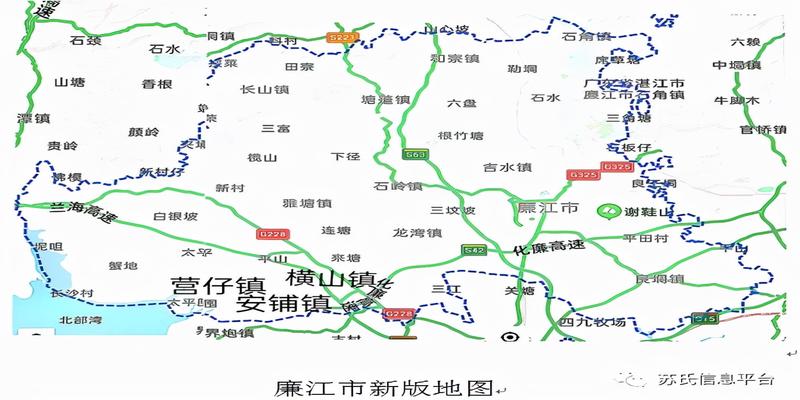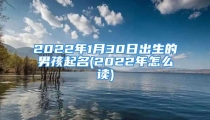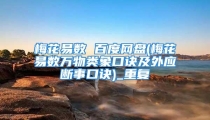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刘小枫作者简介:刘小枫,神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古典诗学、比较古典学、政治思想史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0室,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email?protected]人大复印:《文艺理论》2019年08期原发期刊:《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0191期第113-123页关键词:希罗多德/诗术/雅典民主政制/叙事诗人/政治史学/Herodotus/poiētikē/Atheniandemocracy/narrativepoet/politicalhistory/摘要: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希腊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要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虽然迄今没有定论,但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却是不争的文本事实。ThisarticleissuppertedbytheMajorProjectofNationalSocialSciencesFund(117ZDA320).亚里士多德《诗术》(又译“诗学”“创作学”)名的原文语义,考据家们一度争执不休。因为,poiētikē[诗术]的词干poiē-的原初含义来自行为动词poiein[制作](tomake),带有相当宽泛的作为意涵。有注疏家建议,最好将这个书名径直转写为poietic[art],以便保留“制作”(making)原义,突显thepoet的本义是maker[制作者](Whalley44)。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到,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或者古希腊“诗学”这个语词的用法诞生于雅典民主政制时期。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从政治史学入手,尽可能搞清这个问题的历史语境。我们所要理解的历史语境,并非指现代实证史学所追求的社会史状况,而是当时的优秀头脑面临自己的政治处境时所思索的涉及人世生活根本的哲学问题。如何才能获得古典智识人的智慧,对生活在现代语境中的我们来说,始终是个大难题。施特劳斯30岁出头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友人的信(1932年12月27日)中曾这样袒露自己的看法:我一点不否认,必须历史地哲学思考,即我们必须使希腊人无需使之上升为意识的事实上升为意识。我一点不否认,“素朴”在我们只是一个要求,今天没有谁能够“素朴地”进行哲学思辩。但我要问的是:这种变化是我们原则上比希腊人认知更多(“偏见”问题比“意见”问题更彻底)的一个结果,还是这种变化原则上——即从人之为人所必须认识的知识来看成效甚微,是一种可憎的厄运,强迫我们走一条“不自然的”弯路?(施特劳斯58-59)所谓今天的我们很难“素朴地”思考真正的哲学问题,指我们受到各种现代理论的支配,以至于看不到“人之为人所必须认识的知识”。施特劳斯所说的“素朴”,来自席勒的著名文章《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头几页(席勒403-408),他在信中接着说:素朴的人是自然——对于感伤的人而言,自然性只是一个要求。我们现代人必然是“感伤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感伤的”——以回忆的、历史的——方式探求希腊人“素朴地”探求到的东西;精确地说:我们必须通过回忆将自己带进我们在其中一方面理解希腊人,一方面能够与他们一起“素朴地”进行探求的层面。(施特劳斯59)现代人即“感伤的”人意味着,现代人已经远离“自然”,或者说远离“人之为人所必须认识”的事情。今天的我们要回到“自然的”思考,就得让自己“以回忆的、历史的”方式探求希腊人“素朴地”探求到的东西,这就是笔者上面所说的历史语境。施特劳斯接下来用谜语般的说法指出了这一历史语境的具体含义:现代的反思也好,自我审视抑或深刻性也好,可能不单单揭示了个别事实,而且也泄露了一个希腊人不曾泄露的整个维度(Dimension)。于是,问题仍然是,这个维度具有怎样的[特定品质/尊严]?这果真是一个更彻底的维度?我们真的比希腊人更了解生活之根、生活之不可靠状态?(施特劳斯58)这段话颇值得玩味。要说现代人对“生活之根、生活之不可靠状态”未必比古人理解得深刻和全面,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现代人相信,自由民主的实现就是人的[尊严]的实现。而雅典民主时期的优秀头脑则看到,自由民主的实现掩盖了人世的“生活之根”以及“生活之不可靠状态”的本相,或者说掩盖了人世生活的[特定品质]。然而,古人为什么“不曾泄露”整个维度,又如何做到“不曾泄露”呢?施特劳斯质疑现代人,“我们真的比希腊人更了解生活之根、生活之不可靠状态?”既然古希腊人“不曾泄露”,施特劳斯又何以得知这“不曾泄露的整个维度”呢?要澄清这些困惑,就得追问“作诗”与理解“生活之根、生活之不可靠状态”有怎样的关系。毕竟,施特劳斯借用席勒关于“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来比喻古人与现代人在生存理解上的差异绝非偶然。一、希罗多德与“诗术”让我们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的纪事入手,因为,从今人能够看到的传世文献来看,这两个古希腊语词的“诗”和“诗人”含义用法,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据我看,赫西俄德以及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离我四百年,但不会更早。正是他们把诸神谱系教给希腊人,并给诸神起名,把尊荣和诸技艺分派给神们,还描绘出诸神的模样。至于据说有比这些男人更早的诗人(poiētai),我觉得[这些人]其实比他们生得晚。(《原史》卷253)①希罗多德把赫西俄德和荷马称为“诗人”,但在此之前,赫西俄德被称为“众人的教师”,比他更早的荷马则被称为“[游吟]歌手”(aoidos),都不称“诗人”。所谓“据说有比这些男人更早的诗人”,指传说中的俄耳甫斯(Orpheus)和缪塞俄斯(Musaeus),他们也被称为“歌手”,不称“诗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一983a1-5)中还说:“按照谚语,歌手多谎话”。用今天的说法,“[游吟]歌手”相当于所谓“民间歌手”。为什么希罗多德要改称赫西俄德和荷马为“诗人/制作者”?难道因为“歌手”不制作言辞,从而不能称“诗人/制作者”?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了解,对希罗多德来说,“制作/作诗”意味着什么。希罗多德说,正是赫西俄德和荷马“把诸神谱系教给希腊人”,动词“教给”的原文是“制作”(poiēsantes),现代西文译本未必会把这个动词译为“作诗”,更不用说译成“教给”。笔者译作“教给”,沿用的是王以铸先生的译法(希罗多德134-35),而这种译法很可能意在化用我国古人所谓“制礼作乐”的说法,似乎荷马和赫西俄德堪比我们的圣王周公。但希罗多德的用法有这个意思吗?从前,赫西俄德被称为“众人的教师”,这一称谓表明,古希腊民族的确很早就关切人民的教化,如今叫做关切国民的文明德性。问题在于,即便“民间歌手”或“诗人”都可能是“众人的教师”,但恐怕不能说,这两种教师有相同的灵魂类型,他们传授的德性没有品质差异。笔者想起一件事情,即迄今仍然没有定论的“荷马问题”。17世纪末,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的知识界爆发了著名的“古今之争”,论争焦点之一是:究竟有没有荷马这个制作言辞的高手或“诗人”。论争持续了两百多年,欧洲学界也没有得出让所有古典学家满意的结论(刘小枫92-130)。20世纪初,有位姓帕里(MilmanParry,1902-35年)的美国青年到巴黎大学研修古典学,遇上人类学正在勃兴。他带着现代知识人发明的人类学“技艺”来到南部斯拉夫地区,对当地民间歌手开展田野调查,其间生发出一个奇妙推论:荷马不就是如今在南斯拉夫还能见到的那类民间歌手嘛。据说,这个推论“革命性地”一举解决了“荷马问题”,毕竟,“荷马问题”并非自17世纪以来才诉讼纷纭,而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成为问题(纳吉1-15)。帕里在33岁时不幸因枪击身亡,并未完成其推论——枪击系自杀抑或他杀,迄今仍是个谜。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兼古典学家洛德(AlbertB.Lord,1912-1991年)当时是帕里的助手,差不多30年后,他以《故事的歌手》(TheSingerofTales,1960年)一书完成了帕里的未竟之业。在这部人类学“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奠基作中,洛德开篇就宣称:荷马不过是“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歌手”的名称,当今南斯拉夫民间歌手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马一样,都属于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一部分”(洛德141-226)。“口头诗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民间歌手的演唱绝非仅仅是“口头表演”(oralperformance),毋宁说,他们的演唱即“口头创作”(oralcomposition)。凭靠现代人类学的民俗研究,洛德建立起一条新古典学原理,即“传统的讲故事”(traditionalstorytelling)原理,并应用这一原理来解释所有古代史诗:古典史诗无不出自民间歌手的“口头创作”。按照这条古典学原理,“最平庸”的民间歌手也有权利与最具天才的荷马平起平坐,或者,最具天才的荷马被用来提升“最平庸”的民间歌手。无论哪种情形,“最具天才”与“最平庸”的巨大德性差异消失了,两者获得了诗学上的平等,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如今,我们仰慕当下的民间歌手就行了,因为,即便“最具天才”的荷马,也不过是当时的民间歌手。由此可以理解,帕里-洛德开创的口头诗学为何会被恰切地称为“民主”的美学(洛德19)。笔者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希罗多德说上面那段话时的口吻:他似乎在告诉雅典民主时代的读者,希腊人民所信奉的诸神不仅来自异族,而且是四百年前的两位希腊人“制作”或“编造”出来的。言下之意,希腊人所信奉的诸神未必那么神圣。当今“口头诗学”对古典史诗的去神圣化,在希罗多德身处的雅典民主时代已经可见端倪。在《原史》卷二,希罗多德记叙了海伦被亚历山大从斯巴达抢走后去往埃及的故事(113-15)。希罗多德强调,他的讲述来自祭司们的“说法”,似乎这是“海伦故事”的真实版本。然后他说,荷马明明知道关于海伦的这种“说法”(tonlogon),却“故意放弃这个说法”,用另一个“说法”取而代之,原因是这说法不切合他制作的epopoiiēn[叙事诗]。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荷马在提供另一个“说法”的同时,又刻意让人知道,他知道祭司们的说法,其手法即“在《伊利亚特》中制作出”自己的一套说法(《原史》卷2116.1-2)。随后,希罗多德就引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关于海伦的“诗句”,让读者对比荷马如何既泄露又不曾泄露关于海伦的真实“说法”。希罗多德还说,这些“歌句”清楚表明,“居普利亚之歌”并非出自荷马,而是出自“别的诗人”。②“歌”这个语词的原义是“言辞”(toepos),引申为“故事、歌句”,希罗多德在这里没有用poiēsis[诗]。注疏家通常认为,希罗多德的这段关于海伦故事的说法表明,他不信靠荷马这个权威。其实,与其说希罗多德在质疑荷马的权威,不如说在揭示荷马如何“制作”(epoiēse)他的“叙事诗”。③对比这段说法与前面关于荷马的简扼说法(《原史》卷253),我们应该注意到,希罗多德的纪事笔法有两个特征。首先,希罗多德让自己关于荷马的说法分置不同的文本位置,除非读者留心,否则很难看出其间有什么关联。比如,他在卷二53节说,赫西俄德和荷马“把诸神谱系制作给希腊人”,但没有说如何“制作”;在这里,希罗多德则清楚展示了荷马如何“制作”:既泄露又不曾泄露真相(116-17)。所谓“叙事诗”,其实是荷马这样的高人的制作,尽管其形式是所谓“叙事歌”。如果祭司们关于海伦故事的“说法”代表了某种宗教传统,那么,荷马的“制作/作诗”就无异于改造了这一传统。希罗多德在展示荷马如何“制作/作诗”时,同样采用了既泄露又不曾泄露的方式。因此我们的确很难说,希罗多德是在质疑荷马的权威,也没法说,从古至今所有民族的“史诗”歌手或如今的民间叙事歌手有希罗多德所理解的这种深切著明的荷马“制作/作诗”。许多民族有类似于“居普利亚之歌”的歌句,但荷马不是这类演唱之“歌”的作者,他制作的是“叙事诗”。poiēsis[诗]这个语词在希罗多德笔下出现时的语境(《原史》卷282)也颇有意思,他说,埃及人把“每个月和每一天”分配给诸神,以便由此推断,谁某月某日出生,“谁就会撞上怎样的命运、有怎样的结局,以及会是怎样的[个体]品质”。据注疏家考证,在埃及的法老王时代,埃及人把每月的第一天分配给托忒神(Thoth),第二天分配给何儒斯神(Horus),第三天分配给奥希瑞斯神(Osiris)。这种推算个人品格及其命运的方式,绝非仅仅与诸神信仰有关,也与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古天象学(astrology或称“占星术”)相关。我国古人凭天干地支推算个人禀性及其命运的技艺(所谓“算卦”),差不多与此类似。在今天看来,这套技艺属于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尽管迄今仍然有不少人还相信这一套。希罗多德说,希腊人中也有人“在制作[诗作]中用上这套”(《原史》卷282)。这里所说的“诗作”指谁的诗作不清楚,但可以推断,很可能指荷马或赫西俄德的诗作,因为,这与前面(《原史》卷253)的说法相吻合。希罗多德自己是否相信这套“算卦”不清楚,因为他的记叙口吻似乎表明,这种推算方式不过是某些作诗之人“制作”(等于“编造”)出来的。笔者产生如此推测绝非无事生非,毕竟,希罗多德所生活的时代的确出现了不信传统诸神的苗头。希罗多德的同时代人普罗塔戈拉就曾著文《论诸神》公开宣称,自己会对诸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存而不论——理由是,这问题太艰深,而人生过于短促,没时间探出究竟(拉尔修917)。因此,要说希罗多德把赫西俄德和荷马视为诸神信仰的“制作/编造”者,未见得离谱。毕竟,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政制变革时代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新生的民主政治意识。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希罗多德以怎样的笔法探究过往之事,他的《原史》与在雅典民主政治时期出现的poiēsis[诗]以及poiētēs[诗人]用法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古希腊人的诗术诞生于民主政治时代,那么,希罗多德的《原史》透露出这种诗术具有怎样的品质吗?二、城邦诗人与民主政治《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为了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语境。毕竟,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传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我们值得问,为何雅典民主时代会出现这样的用法?智术师们的发明?智术师的文献大多轶失,无从查考。即便是普罗塔戈拉(公元前490-前420年)的发明,他仅年长希罗多德几岁,也未见得有资格与希罗多德争夺这种用法的发明权(Ford139-40)。也许,与其说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是希罗多德或某个智识人的发明,还不如说这是雅典民主政治时期的俚俗说法。毕竟,在当时的雅典城邦生活中,戏剧制作和演出已经相当活跃。我们应该意识到,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去世时,希罗多德还不到30岁,而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前406年)仅比希罗多德年长十多岁,据说两人交谊甚笃。希罗多德笔下的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来自雅典的生活现实,符合他的纪实风格。克腊提努斯(Cratinus,公元前519-前422年)史称雅典三大喜剧诗人之首,与埃斯库罗斯双峰并峙,所谓的poiēma[戏剧作品/制作品]这个语词,最早就见于克腊提努斯笔下(fr.198)。希罗多德的阅历也伴随着雅典民主戏剧的变迁:当时的声誉堪与索福克勒斯比肩的喜剧诗人欧珀利斯(Eupolis,公元前446-前411年)和苏格拉底的诤友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前386年)比希罗多德年轻整整一辈。④在阿里斯托芬笔下,出现了melopoios[歌曲诗人]和tragōdopoios[悲剧诗人]的用法;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则有humnopoios[赞美歌诗人]的用法(Ford134)。可以说,希罗多德的纪事意识与雅典戏剧诗人的“作诗”意识有值得注意的同时代关联。雅典人用poiētēs指称当时的剧作家,用poiēsis指称他们所制作的戏剧,相当于今天我们说“搞戏剧”或“做戏”。希罗多德在《原史》中把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称为logopoios[制作故事者](《原史》卷2143),今天的文史家把这个词译为“史家”,其实,希罗多德不过把“搞[制作]戏剧”这个俚俗说法用到自己的前辈身上而已。雅典戏剧源于如今所谓民俗宗教的节庆传统,与民主政治的兴起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民俗性的宗教节庆表演演化成poiētēs[诗人]的“制作”(poiēsis),恰恰发生在雅典民主政制的历史时刻,要说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或者古希腊“诗学”诞生于民主政制并不为过。问题在于,无论悲剧诗人还是喜剧诗人的戏剧“制作”(poiēsis[诗]),都没有把雅典民主呈现为如今所谓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政制理想,反倒呈现为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宗教问题。要说民主的雅典政制具有世界史意义,那么,雅典诗人的poiēma[制作品/戏剧作品]同样具有世界史意义,而其意义就在于:后世之人不得不跟随他们一起思考民主政制的德性品质问题。雅典民主是雅典城邦历时近三个世纪的政治大变局的结果,要历史地认识雅典民主的来龙去脉,就需要从政治史学角度把握雅典城邦如何从君主制到贵族制然后到僭主制再到民主制的整个历程。显然,要做到这种史学式的把握非常不容易。近百年来尤其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学界的雅典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最早面对这一历史认识问题的是雅典民主时期的优秀头脑。通常认为,第一部雅典政治史出自亚里士多德手笔:他的《雅典政制》从德拉孔改制起笔,记叙了雅典城邦从君主制到民主政制的历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希罗多德的《原史》才算得上记叙并思考雅典城邦政治变迁的开山之作。问题的麻烦在于,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迄今没有定论(吴小峰编71-109;梅耶345-51)。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是,《原史》中有太多凭靠叙事笔法建构(或虚构)出来的故事而非史实,为澄清这些故事的历史真相,如今的实证史学家使尽浑身解数,最终仍然可能无功而返。比如,希罗多德开篇讲述的“偷看王后裸体的代价”故事(《原史》卷18-12),今人很难通过发掘史料或田野考古搞清是否确有其事,抑或不过是希罗多德编起来说的(《凯诺斯:古希腊语文读本》230-33)。公元前621年,贵族出身的司法执政官德拉孔(Dracōn)为雅典城邦立法,史称雅典城邦从君主制转向贵族制的标志。德拉孔改制的后果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了贵族手里,以至贵族与平民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又引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两次政治改革相距不到30年,可见雅典城邦虽小,却在短时期内持续剧烈动荡。雅典动荡的根源,并非仅仅来自城邦内部的阶级冲突,泛希腊城邦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很可能是雅典动荡更重要的根源。最有力的证据恰恰来自《原史》的叙事,尤其是希罗多德的叙事万花筒般的谋篇布局。《原史》以如下问题开篇:为应对波斯人的进逼,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不得不考虑与爱琴海西岸的希腊陆地上相互敌对的城邦中的哪个城邦结盟。换言之,《原史》展示的地缘政治背景,绝非仅仅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泛希腊城邦之间的内部兼并同样重要。简扼来讲,德拉孔改制之前,斯巴达发起的第二次墨斯瑟尼亚战争(theSecondMessenianWar,公元前640-前630年)已经成功向伯罗奔半岛西南部(即墨斯瑟尼亚地区)扩张,从而开始坐大。在此之前,泛希腊地区最发达的城邦是科林多,还轮不上雅典。公元前657年,那里也发生过一场重大政治事变:贵族出生的居普瑟鲁斯(Cypselus)推翻巴克基亚德家族(theBacchiadfamily)的王权统治成为“僭主”。可以说,这次政变是科林多为应对斯巴达崛起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因为,公元前730至前710年,斯巴达曾发起第一次试图夺取墨斯瑟尼亚的战争,明显威胁到科林多的地缘政治优势。居普瑟鲁斯执政30年,科林多不仅得以继续保持泛希腊地区的政治优势,经济实力也进一步增强。公元前625年,居普瑟鲁斯的儿子珀瑞安德(Periander)接掌政权,延续僭主统治,在其治下,科林多的手工业和制造业相当繁荣。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带来经济繁荣,是现代学人制造出来的传说。在希罗多德笔下,居普瑟鲁斯虽然是僭主,但治国有方,压制反对派毫不手软,却得到人民广泛拥戴;其子珀瑞安德的僭主统治也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而且执政长达40年(至公元前585年去世),却遭到人民憎恨。由此看来,希罗多德笔下的僭主有好有坏,没法一概而论。tyrannos[僭主]本是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外来词,原义为“统治者”,并不带贬抑,但在《原史》中,“僭主”的道德形象虽然有时显得含混,“僭主”这个语词的用法基本上带贬抑,与basileus[王]的褒义用法明显有分别。要说何谓真正的“王者”是《原史》探究的重大主题,不会离谱。可是,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高超,他本人对僭主的态度究竟如何,古典学家们直到今天还争执不休(吴小峰编53-70)。如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文学笔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原史》在“制作/作诗”王者问题。进一步说,柏拉图的《王制》(又译《理想国》)的主题是“王者”问题,但为何两头两尾(卷二结尾和卷三开头及卷十开头)都在讨论“作诗”问题,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德拉孔改制后,雅典仍然在斯巴达与科林多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两面夹击处境中处于劣势,梭伦(Solōn,公元前638-前559年)改革后的雅典并没有实现长治久安,反倒出现了僭政,以至今天有古典学家不得不说,尽管梭伦是伟大的立法者,但他也是“政治失败的典型”。因为,他的改革虽然具有民主化取向,却为僭政铺平了道路(麦格琉156-69)。公元前560年,梭伦的姨兄庇希斯特拉图(Peisistratos)有一天先自己把身上的衣服撕烂,然后给自己身上抹满猪血,气喘吁吁跑到公民大会上说,“人民的敌人对他行刺”,要求大会同意他组成一支卫队保护自己。公民代表们同意了,庇希斯特拉图随即组成一支“棍棒队”(korunēphoroi)夺取政权,成为雅典第一个成功揽权的僭主(《原史》卷159.5)。希罗多德对庇希斯特拉图的起势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被有的古典学家拿来与索福克勒斯借虚构的“作诗”探究“权力”(Power)问题的方方面面相提并论,似乎希罗多德的“讲故事”与戏剧诗人的“作诗”别无二致(吴小峰编211-45)。倘若如此,这种相似性恰恰在于,古典学家迄今仍在争议希罗多德对庇希斯特拉图僭政的态度。有人说,在希罗多德笔下(《原史》卷159),庇希斯特拉图执政期间(公元前561-527年),雅典人没有自由,而且整个城邦被搞得“四分五裂”;凭靠同一文本有人则说,在希罗多德笔下,庇希斯特拉图的僭政给雅典带来了秩序,并取得了造福城邦的优良政绩(吴小峰编121)。庇希斯特拉图死后,其子希琵阿斯和希帕库斯继续推行僭政,随后发生了著名的刺杀希帕库斯事件,接下来的激烈政争催生了雅典的民主时代(《原史》卷6123):公元前510-前508年,史称“雅典民主之父”的克莱斯忒涅(Cleisthenēs,约公元前570-前508年)推行政改,确立“平等参政权”(isonomia)原则,开启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雅典民主政制时期的旅程——公元前500年,雅典城邦设立狄俄尼索斯戏剧节(Dionysia)。今天的我们难免好奇:克莱斯忒涅为何要推行“平等参政权”?他不是出身贵族豪门阿尔喀迈俄尼德(Alcmaeonid)宗族吗,难道他有民主理想?其实,克莱斯忒涅也是个僭主,从《原史》中我们读到,克莱斯忒涅提倡“平等参政权”不过为了拉拢雅典民众,以便对抗其政争对手——同样出身于贵族豪门的伊萨哥拉斯(Isagoras)。换言之,“平等参政权”原则不过是有政治抱负者之间政争时手中的一张牌。现代的实证史学家未必这样看,当代日本学界最著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依据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立场来解释“平等参政权”,同样如此(Ober68-75;柄谷行人14-48)。三、希罗多德的“作诗”与马拉松之战围绕希罗多德是否信奉“自由民主”的争讼,迄今没有了结(吴小锋编125-26),问题在于,即便希罗多德心仪雅典民主,他也并非像如今的史学家那样,凭靠这种信仰来修史。毋宁说,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原史》记叙了克莱斯忒涅施行民主改革之后的雅典与波斯王国的战争,由于当时的雅典城邦仍然身处劣势,却击败波斯王国的进犯,人们往往以为,《原史》意在证明西方民主制何以能够战胜东方君主制,或者民主制何以优于君主制。情形真的如此吗?公元前490年著名的马拉松(位于阿提卡东北海岸)之战是后来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85-479年)的直接“成因”:当时,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I,公元前550-前486年)本来蛮有胜算,未料遭遇惨败,发誓要雪耻。那么,马拉松之战的起因又是什么呢?专制的波斯王国肆意侵略希腊大陆?希罗多德让我们看到,波斯进犯希腊半岛的真正起因是惩罚雅典人出尔反尔。原来,伊萨哥拉斯在公元前508年成为雅典执政官,由于克莱斯忒涅凭靠许诺“平等参政权”获得雅典民众支持,他感到难以掌控政局,便邀请斯巴达国王率军介入雅典内政,压制克莱斯忒涅派势力。没想到克莱斯忒涅成功动员雅典人击退斯巴达人,还从伊萨哥拉斯手中夺得政权(《原史》卷572)。然而,斯巴达王国的威胁并未解除,为了求得战略平衡,克莱斯忒涅向爱琴海东岸的波斯王国寻求保护。长期以来,雅典的头号敌人不是异族的波斯人,而是同族的斯巴达人。当时,波斯王国正在巩固从吕底亚王国手里夺取的爱琴海东岸地区(伊奥尼亚),尽管在大流士眼里,雅典小城微不足道,仍然同意提供保护。雅典使者献上泥土和水,作为信物表示臣服于波斯王国(《原史》卷573)。伊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僭主臣服波斯王国已经近半个世纪,公元前499年,伊奥尼亚地区突然爆发针对波斯王国的大规模起义,史称“伊奥尼亚叛乱”(Ionianrevolt)。直到今天,古史学家仍然没法最终确定,伊奥尼亚希腊人的起义究竟是反抗波斯王国还是反抗僭主的实际统治,因为希罗多德的记叙颇为含糊(《原史》卷535-38)。伊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联手起义时,派使者向爱琴海西岸的雅典和斯巴达求助。斯巴达国王看了使者带来的地图,觉得率军进击波斯王国根本不可能,没有理睬自己的希腊同胞的求助。雅典此时已经是克莱斯忒涅施行民主改革后,对外军事行动得靠公民投票决定。希罗多德没有说,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出兵援助伊奥尼亚地区的起义是为了民主理想或反抗异族统治,毕竟,从“国际法”上讲,雅典人自己这时也是波斯王国的臣民(《原史》卷569-70)。雅典与另一个小城邦组成的联军一度进击波斯本土,但丝毫没有伤及波斯王国筋骨。公元494年,大流士率军成功镇压起义,然后决定惩罚雅典人:当初你雅典城邦为了抗衡斯巴达人主动称臣,如今又掺和伊奥尼亚的希腊人闹事,哪有这种出尔反尔的道理——这才有了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在靠近马拉松的村庄登陆。直到今天,《原史》的探究志趣究竟是什么,即便对希罗多德专家来说,也仍然还是一道不易回答的难题。由于希罗多德以其高超的叙事笔法一手制作了这道难题,不断有古典学家提出,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在“作诗”,而非现代实证史学意义上的撰史。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逼近这样的问题:希罗多德的“作诗”与民主的雅典崛起为地中海大国的关系。《原史》记叙的历史时段大致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80年之间,而成书则大约在公元前430年。从公元前480年到《原史》成书的公元前430年,足足有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爱琴海周边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雅典崛起为大国,与此同时,雅典民主朝着激进化方向发展。我们值得意识到,对希罗多德这样的智识人来说,雅典崛起吸引他,绝不仅仅因为雅典成了区域“强国”,当时的戏剧诗人已经“制作”出成文作品,同样重要。古典学家们公认,雅典民主的激进化及其所引发的政治争纷,是《原史》写作的背景,不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恰恰理解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吴小峰编211)。我们知道,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作品中,民主政治引发的政治-宗教问题极为尖锐——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是绝好的证明,以至于这部剧作可以被视为雅典政治思想史的经典文本(梅耶133-236)。戏剧诗人的“戏剧制作”[作诗]据说是为了让雅典公民参与思考眼下的政治变革,倘若如此,《原史》与当时的雅典戏剧一样,很有可能也是为雅典公众制作的。人类学古典学家甚至推断,《原史》的叙事具有民间说书风格,希罗多德很可能对雅典听众朗读过某些部分。当时的所谓“读书”,其实就是由人念书给“读书人”听。希罗多德把几十年前甚至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编成故事来说,与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或《波斯人》让过去发生的事情成为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不同。用今天的话来讲:埃斯库罗斯是在“搞戏剧[作诗]”,希罗多德是在说评书——两者都有可能影射雅典的政治现实。纪事和悲剧因共同起源于史诗而连在一起,因使用可比较的而且经常相同的素材以及它们的道德意图而连在一起。因此,专属于一种类型的阐述相当经常地适用于另一种类型,而且那些试图影响其读者的情感的史家会被人说成是假冒的悲剧作家,并不十分令人惊奇。(《西方古代的天下观》53)马拉松之战结束后,雅典因击败波斯人而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开始崛起,从战场上下来的某些政治精英组成激进民主党,其领导人厄菲阿尔特(Ephialtes)把政治目标锁定为:以雅典公民大会取代卫城山议事会的治权,实现直接民主。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遭反对派刺杀身亡,时年30多岁的伯利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29年)接替他继续彻底民主化的未竟之业——这时希罗多德20岁出头。公元前458年,雅典公民大会终于取代卫城山议事会,获得掌控城邦的实际权力。无独有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也在这一年完成制作。十年后,索福克勒斯完成了《埃阿斯》的制作(公元前447年)。这时的雅典已经在谋求地中海的领导权,甚至在隔得老远的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图里澳也建立了殖民地,伯利克勒斯委托外邦来的智术师普罗塔戈为该地制作法律(公元前444年),随后不久,索福克勒斯完成了《安提戈涅》的制作(公元前441年)。在整个这段时期,雅典的崛起自然会引起斯巴达的忌惮,两个区域大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就是希罗多德制作《原史》时的历史语境,他的笔端若没有染上时代气息,那才奇怪。据古典学家考订,希罗多德大约在公元前447年左右到的雅典,4年后(公元前443年)与普罗塔戈拉一起前往图里澳,主持这个雅典殖民地的建设。在雅典期间,希罗多德与索福克勒斯成为好友——这位悲剧诗人曾为希罗多德写过颂诗。九年后(公元前434年),希罗多德因图里澳与雅典关系变冷重新返回雅典。据推断,希罗多德到图里澳不久就动笔写《原史》,直到去世都没有完成,停笔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30至424年之间,与欧里庇得斯完成《美狄亚》的时候差不多(卢里叶)。戏剧诗人的剧作是为在雅典公民面前上演而作,剧作中的故事即便改编自古老传说,也会让雅典公民联想到眼下自己正在经历的政治变革。古典学家确认,希罗多德记叙的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故事(《原史》卷135-45)明显在模仿悲剧诗人,而他记叙的涉及权力争斗的故事,与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主题有惊人的一致(《原史》卷3119)。问题在于希罗多德是否属于民主派阵营,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算得上自由民主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古典学家迄今没有取得共识:一些古典学者认定,希罗多德明显具有民主倾向,但质疑这一看法的也大有人在,双方都不无文本依据。显然,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希罗多德的高超叙事笔法即“作诗”让人难以看出他的政治倾向。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著名细节。克莱斯忒涅在雅典推行“平等参政权”原则后,雅典城邦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打了一系列胜仗,成了区域强国。紧随这段雅典崛起的记叙之后,笔法向来节制的希罗多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于是,雅典强盛起来。显然,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所有地方,平等议政权(isēgoriē)都是高尚的事;因为,当雅典人受僭主统治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自己的邻人更优;但现在呢,他们挣脱了僭主们的桎梏,马上变得出类拔萃。显然,人们由此看到,当他们任人使唤时是为主子做工,一旦他们得到自由,则个个热切地为自己的事尽心竭力。这便是雅典的状况,而忒拜人呢,则派人去德尔菲问神,因为他们想要报复雅典人。(《原史》卷578)这段说法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是isēgoriē,这个语词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标志或符号,指公民有参与城邦事务的议政权利。若译作“自由发言的权利”(therightoffreespeech)会导致误解,让人以为与如今的“言论自由”是一回事。显然,首先得有政治上的平等,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权利”,因此译作“政治平等”较为明晰,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或财富分配上的平等。从文脉来看,希罗多德似乎要得出这样的推论:雅典人推翻僭政施行民主政制,是雅典人在国际冲突中取胜的根本原因。不少古典学家还认定,这段话证明希罗多德具有民主信念,因此引用率特别高。“得到自由”与“任人使唤”形成对比,“为自己的事尽心竭力”与“为主子做工”形成对比,同样如此。换言之,这段话有明显的雅典民主意识形态修辞色彩,我们能设想希罗多德会如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吗?反复体味就会发现,连续两次出现“显然”(dēloi),口吻似乎有些夸张。雅典人一旦获得“自由”就会变得“出类拔萃”,亦即比自己的希腊同胞“更优”,但蹊跷的是,这种“出类拔萃”或“更优”不过是“个个热切地为自己的事尽心竭力”。用今天的话来讲,雅典公民获得的“自由”相当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而非参与公共生活为共同体的利益尽心竭力。从逻辑上和常识上讲,“热切地为自己的事尽心竭力”何以能让一个城邦公民变得“出类拔萃”,也颇令人费解。何况,希罗多德在结尾时笔锋一转,说忒拜人针对雅典的政制变革“派人去德尔菲问神,因为他们想要报复雅典人”。我们应该感到奇怪:为什么忒拜人要因为雅典施行民主政制而“报复”呢?最让人起疑心的是:如果僭政既残暴又专制,那么,为何雅典民主又是克莱斯忒涅的僭政带来的呢?雅典在施行民主制之前经历了一连串僭政,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既然如此,这段话中所展现的“平等议政权”和“自由”与僭政的对立,就很难被视为认真的说法,反倒有可能是反讽。无论如何,这段颂扬雅典民主的著名说法,很难被视为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他越是说“显然”,实际上恰恰可能并不“显然”。有古典学家推测,希罗多德在这里的修辞极有可能是在迎合雅典听众。还有一种推测也不无道理:如果与希罗多德在书中其他地方关于自由和僭政的说法对比,那么,人们就能发现,希罗多德仅仅是在呈现雅典城邦的意见,正如他也会呈现波斯人的政治意见,以展示人世政治生活的本相。希罗多德的这段言辞也被视为对如下政治理论的最早表达:一个政治体施行什么制度,与其外交政策乃至政治体本身的命运紧密相关。在随后的大思想家和纪事家如亚里士多德和珀律比俄斯那里,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展开。⑤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思考:一个政治体哪怕再小,是否能够通过基于平等权利的“议政”为政治体的兴衰提供可靠保障?民主的雅典打赢了这场抵抗波斯人的战争,不等于民主政体是任何政治体在地缘政治角力中克敌制胜的万能法宝。随后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雅典的地缘政治态势并不妙:公元前433年,雅典与科林多发生冲突,次年,雅典对麦加拉实施经济封锁。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地区,雅典海军则突袭伯罗奔半岛,第二次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希罗多德离世之时大约在公元前425年,当时《原史》并未杀青。记叙这场战争的修昔底德说:关于战争中完成的行动,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既不能把偶然听到的见闻都写下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写,而是对我自己的亲身见闻和别人的传闻尽可能准确地研究每个细节。探究是辛苦事儿,由于偏爱两方中一方或者记忆力不同,亲历同一行动的人们会有不同的说法。我的著述没有故事,可能会使其不那么悦耳。(修昔底德1.22)“把偶然听到的见闻都写下”和“我的著述没来的呢?雅典在施行民主制之前经历了一连串僭政,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既然如此,这段话中所展现的“平等议政权”和“自由”与僭政的对立,就很难被视为认真的说法,反倒有可能是反讽。无论如何,这段颂扬雅典民主的著名说法,很难被视为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他越是说“显然”,实际上恰恰可能并不“显然”。有古典学家推测,希罗多德在这里的修辞极有可能是在迎合雅典听众。还有一种推测也不无道理:如果与希罗多德在书中其他地方关于自由和僭政的说法对比,那么,人们就能发现,希罗多德仅仅是在呈现雅典城邦的意见,正如他也会呈现波斯人的政治意见,以展示人世政治生活的本相。希罗多德的这段言辞也被视为对如下政治理论的最早表达:一个政治体施行什么制度,与其外交政策乃至政治体本身的命运紧密相关。在随后的大思想家和纪事家如亚里士多德和珀律比俄斯那里,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展开。⑤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思考:一个政治体哪怕再小,是否能够通过基于平等权利的“议政”为政治体的兴衰提供可靠保障?民主的雅典打赢了这场抵抗波斯人的战争,不等于民主政体是任何政治体在地缘政治角力中克敌制胜的万能法宝。随后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雅典的地缘政治态势并不妙:公元前433年,雅典与科林多发生冲突,次年,雅典对麦加拉实施经济封锁。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地区,雅典海军则突袭伯罗奔半岛,第二次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希罗多德离世之时大约在公元前425年,当时《原史》并未杀青。记叙这场战争的修昔底德说:关于战争中完成的行动,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既不能把偶然听到的见闻都写下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写,而是对我自己的亲身见闻和别人的传闻尽可能准确地研究每个细节。探究是辛苦事儿,由于偏爱两方中一方或者记忆力不同,亲历同一行动的人们会有不同的说法。我的著述没有故事,可能会使其不那么悦耳。(修昔底德1.22)“把偶然听到的见闻都写下”和“我的著述没有故事,可能会使其不那么悦耳”云云,都是在指责希罗多德这位前辈。修昔底德仅比希罗多德小14岁,据说他年轻时听希罗多德当众朗读《原史》时曾泪流满面。如果《原史》不是诗作,希罗多德的朗读恐怕不会有如此奇效。施特劳斯阅读古希腊经典史书的首要收获是,他发现所有这些经典史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一样,即他们在“作诗”,而非在纪实: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并不是史学家——当然不是,而是显白的“劝导性作品”的作者。他们的史书正是柏拉图在《王制》卷三中所推荐的青年课程:这是些散文作品,其中行事的阐述超过言辞,而悲剧家——举例来说不仅不用散文写作,而且完全是说理。作者在其中完全隐藏起来的柏拉图式的对话,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属于更高一个层次。(施特劳斯281)希罗多德的叙事表面上看来没有隐藏作者自己,因为他写的是纪事而非戏剧或对话,然而,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仍然隐藏了作为作者的自己,尽量让故事本身说话。我们还看到,希罗多德让作为讲述者的“我”与故事之间有一种极富生气的关系。注释:①本稿所引希罗多德《原史》,均出自笔者自己的译文(随文注希腊文编本标准编码)。译文依据JosefFeix希德对照本,笺释依据Asheri,亦参How.②这里的希腊文原文并未出现poiētēs,而是省略用法,见《原史》卷二第117页。③荷马对纪事[史书]作家的影响,参见Strasburger。④克腊提努斯和欧珀利斯的喜剧均仅存辑佚残篇,见Kassel,比较Harvey。⑤比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五4.8(1304a);卷六7.1(1321a);珀律比俄斯,《罗马兴志》,卷六第3页。参考文献:[1]Asheri,David,etal.ACommentaryonHerodotusBooks.Vol.I-IV.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2]Ford,Andrew.TheOriginsofCriticism:LiteraryCultureandPoeticTheoryinClassicalGree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2.[3]Harvey,DavidandWilkinsJohn,eds.TheRivalsofAristophanes:StudiesinAthenianOldComedy.London:DuckworthandtheClassicalPressofWales,2000.[4]Herodot.Historien(Griechisch-Deutsch).Ed.JosefFeix.JosefHrsg.München:ErnstHeimeran,1963.[5]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983年.[Herodotus.Histories.Trans.WangYizhu.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1959/1983].[6]How,W.W,andWells,J.ACommentaryonHerodotus.Vol.I-II.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7]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潘世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Karatani,Kojin.OriginsofPhilosophy.Trans.PanShisheng.Beijing:CentralCompilation&TranslationPress,2015].[8]Kassel,Rudolf,andColinAustin,eds.PoetaeComiciGraeci.IV.Berlin:WalterDeGruyter,1983.[9]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Laertius,Diogenes.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Trans.XuKailaiandPuLin.Guilin: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2010].[10]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Liu,Xiaofeng.ClassicStudiesandtheConflictsbetweentheAncientsandtheModerns.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2017].[11]刘小枫编修:《凯诺斯:古希腊语文读本》(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Liu,Xiaofeng,ed.Kairos:APhilologicalTextofAncientGreek.Vol.1.Shanghai: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2013].[12]——:《西方古代的天下观》,杨志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WesternAncientViewofTianxia.Trans.YangZhicheng,etal.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2018].[13]罗门·雅科夫列维奇·卢里叶:《论希罗多德》,王以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Лурье,C.Я.OnHerodotus.Trans.WangYizhu.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2018].[14]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Lord,AlbertBates.TheSingerofTales.Trans.YinHubin.Beijing:ZhonghuaBookCompany,2004].[15]克里斯蒂安·梅耶:《古希腊政治的起源》,王师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Meier,Christian.TheGreekDiscoveryofPolitics.Trans.WangShi.Shanghai: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2013].[16]詹姆斯·麦格琉:《古希腊的僭政与政治文化》,孟庆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McGlew,James.TyrannyandPoliticalCultureinAncientGreece.Trans.MengQingtao.Shanghai: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2015].[17]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Nagy,Gregory.HomericProblems.Trans.BamoQubumo.Beijing:ChinaSocialSciencesPress,2008].[18]Ober,Josiah.MassandEliteinDemocratic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thePowerofthePeopl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19]Parry,Adam,ed.TheMakingofHomericVerse:TheCollectedPapersofMilmanPar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20]弗雷德里希·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选》,范大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Schiller,Fridrich.AnAnthologyofFridrichSchiller’sAesthetics.Trans.FanDacan,etal.Beijing: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2015].[21]Strasburger,Hermann.HomerunddieGeschichtsschreibung.Heidelberg:Winter,1972.[22]列奥·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重订本),迈尔夫妇编,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Strauss,Leo.ReturntoClassicalPoliticalPhilosophy.Eds.HeinrichMeierandWiebkeMeier.Trans.ZhuYanbingandHeHongzao.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2017].[23]修昔底德:《伯罗奔半岛战争志》,李世祥译(未刊稿)。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Thucydides.ThePeloponnesianWar.Trans.LiShixiang.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forthcoming].[24]Whalley,George.Aristotle’sPoetics:TranslatedandwithaCommentary.Buffalo: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7.[25]吴小峰编译:《希罗多德的王霸之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