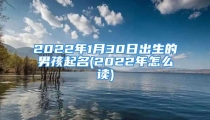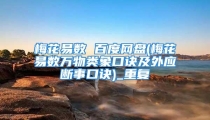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吴玉琴
和女儿结伴去图书馆,老远就听到锣鼓的声响。快到广场,远远看去,人头攒动,原来是一群老人在扭秧歌。嘱咐女儿去看书,我也站到了观望的人群中。
“咚咚咦咚呛,咚咚咚呛咦咚呛……”秧歌队里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踏着鼓点,走着轻快的十字步,一手执桃红的扇子随腕转翻飞,一手执翠绿的绸带随臂绕起舞。没有袅娜的身姿,但这红红绿绿的色彩和老人们快活的精气神却把整个秧歌队舞得红红火火。队伍中,有一位很特别的老人,每一个动作都很到位,颔首抬眼,抬脚拧跨,折扇舞绸,灵动自如,像是领队。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姑姑。
刚刚解放,姑父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姑父有文化,有胆识,年纪轻轻就当上团委干部。下乡搞文化活动,在一支朝气蓬勃的秧歌队伍里,有一位姑娘貌不惊人,但舞得最热辣,舞得最欢快。这位姑娘就是我的姑姑。姑姑眼睛不大,脸瘦长,实在算不得好看。姑姑不识字,对歌舞的领悟却天赋极高。据姑父说,当时看姑姑扭秧歌,都看得入迷了。后来有人给介绍对象,姑父作为干部,完全可以找一个家世、相貌样样出众的姑娘,可是姑父却说:我就看上那个剪着齐耳短发,刘海梳得齐齐的那个扭秧歌的。姑姑原本已经被爷爷许配给婶子的侄儿了,但是姑姑仰慕姑父的才华,宁愿跳井也不嫁给婶子的侄儿。姑父为姑姑辞了团委的职务,回家做了农民。这一段秧歌一样热烈浪漫的爱情,也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婚后姑姑凭着自己的温顺贤良和勤劳能干照顾着大家庭的老老少少,再也没机会走入她喜爱的秧歌队。
姑姑最后的几年,一度半身不遂。每一次去看姑姑,姑姑都会和我们念叨:“社会越来越好了,我却不中用了,常常会梦见以前扭秧歌的日子……”十年前,姑姑离开了我们,秧歌也一度被我遗忘。
湿热的眼睛依旧停留在秧歌队伍里。那上下翻飞起舞的彩扇和绿绸又把我带到童年。
上小学时,每到春节前一个月,村里能歌善舞的人就会组织起本村的人或者前后村的人,集体排练,等到正月挨家挨户拜年演出。从正月初四开始,一群男女老少扭起来了。一会排成“龙摆尾”,一会犹如“梅花盛开”,一会好像“老虎扬尾”,一会好似“大灯笼”,一会好像朵朵枣花……红与绿的扇子在装扮得姹紫嫣红的姑娘媳妇手中飞起来转起来,观者不是眼花缭乱,而是眼神跟着扇子起落,不知道最后落在何方。后生们穿着各色服装,腰里绑着两米长的红绸,进进退退的绕着十字步,手里舞动着长长的红丝带,犹如一条条蛟龙,一会朝前冲去,一会拔地而起,一会忽从天降……长龙一样的秧歌队伍亦步亦趋,每一个人的手、脚、头,全都是活的、动的,让人眼光不知道放在哪里,放在哪里都是恰到好处的。
每到一家,秧歌表演十分钟左右,就停下锣鼓开始唱“小曲”。小曲平仄押韵,朗朗上口,前几句总结这家人过去一年光景的好坏,后几句祝福来年人人期待着的兴隆安康。如果谁家小两口爱打架,小曲还调侃几句,惹得围观者哄堂大笑,小两口不言语,只顾红着脸发糖发烟。
“小曲”唱毕,两只威风凛凛的狮子摇着脑袋,摆着身子,张着血盆大口,或平空后仰翻滚,或高台俯卧衔球,或单狮走桩,或双狮争戏,或扮鬼脸。起势、奋起、迎宾、施礼、作揖……将威武之狮的喜、怒、哀、乐之状舞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一时间,场内场外一只只眼睛齐聚在狮子身边。忽然,一个转身,狮子落地,场内场外齐声欢腾,掌声、喝彩声震荡着天空,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狮子开路走出院门,秧歌队走入下一家。
“咚咚锵、咚咚锵……”儿时乡村的年,秧歌在院子里,脑畔上、玉米架上、树杈上,人头攒动,喜气洋洋。秧歌在麦场上,时而粗犷奔放,能使河流为之激扬动荡;时而稳步柔美,能使无数人为之心醉;时而缓和细腻,能使山岳为之倾倒。
无法想象,这样简单的舞蹈,这样单调的音乐竟能够撼动那么多人的神经。不单单是因为这是一种舞蹈或是一种音乐,而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以来的积淀,这是民众用来表达情感,送祝福祈平安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这让我想到于丹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最经典的东西,往往也是最朴素的东西。秧歌,之所以有众多的舞者,众多的观者应该就是源于此吧。
偷眼看围观的人群,有老有少,有些人目不转睛,有些人斜倚身子,一只脚也在和着节拍,如同人在其中。我不禁暗暗感动,想起姑姑,我默默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精彩的时代。是啊,只有国泰民安,国富民强,老百姓才会尽情地享受小美之欢,用如此喜闻乐见的民众娱乐项目舞出最简单、最朴素、最真挚的节拍,舞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