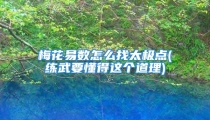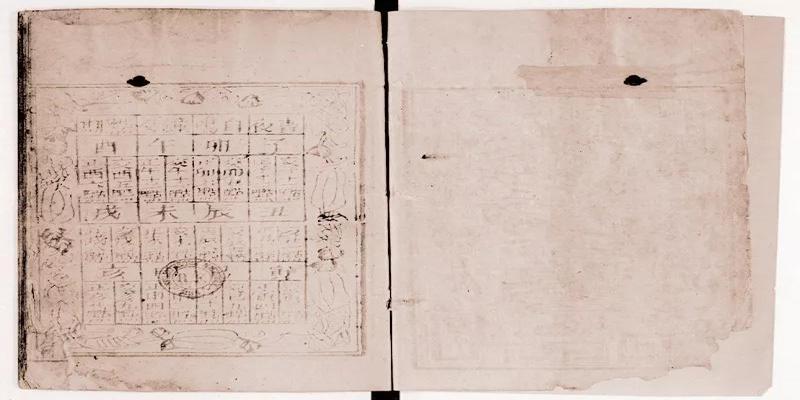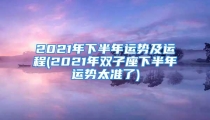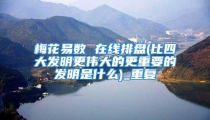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子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是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条。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几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一直用的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开始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拣。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必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拣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是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和第三个孩子一起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和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 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杈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 --杂面;米是红色的---高梁。加上红尊、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愤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着雪白的挂面去邻居家讨换乌涂涂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来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娘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时,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饭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骗子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喝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的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
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顿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1米,铲子换成了铁锨。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找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声,一把把我从锅台上拿了下来。前两天看到一则广告,一个螃蟹对另一只说,哥们儿,被人煮了吧!怎么听怎么耳熟。
这事怎么好跟人家小战士发火呢,母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的一声把饭桶围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排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4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戳。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轻捞慢起。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不到一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齿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
现在回想起部队的饭菜,隐隐约约觉得五香粉的味道很冲。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87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色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下不备,贴着我耳朵说,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
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饲养员,饲养员掰了一块豆饼抓了两把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进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找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一天去3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人间自有副食在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有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一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还有一种,是草本植物,叶子酸酸的,搞不清学名,随伙伴叫它“酸不丢”,偏偏喜欢长在坟头上。伙伴总喜欢带我去他爷爷的坟上采,顺嘴就吃起来,半夜大口大口吐酸水,还梦见他爷爷说:活该!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总说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 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儿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了一遍。
过在嘴里的春节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250克花生,100克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按糖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的话,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柜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到秤盘里,这里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了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赔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炸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的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以吃会友
春节一过,日子又清淡起来。
母亲开动脑筋,自制零食给我们解馋。
做米饭多焖一会儿,结出一张锅巴;柴草将熄的时候,扔进去一个白薯或土豆,烤熟以后,香味冲鼻。
肚子里油水不够,常常是晚上还没睡着,又饿了起来。所以我最忌讳晚上看电影时出现吃的场面。
对许多人,这些场面肯定会历历在目。
《沙家浜》里的芦根、鸡头米。
《地道战》里假武工队吃的煮鸡蛋。
《战友》里小孩手捧的杨梅。
《小兵张嘎》里嘎子吃的玉米和胖翻译吃的西瓜。
《鸡毛信》里鬼子们吃的烤羊腿......
前些日子失眠,半夜爬起来看 VCD,是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刚看个头就饿了,打开冰箱,拿出一整只烤鸡,撕扯着吃掉,立时神清气爽,一下就进人了艺术的殿堂。
我写吃,是记录细碎的经历。作家们写吃,纯是艺术的享受。不吃便已陶醉。
阿城的《棋王》中,有两处吃让人过目难忘。
一是王一生吃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
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的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
二是知青们吃蛇。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骨在碗里。我又把蒸熟的茄块儿端上来,放少许蒜和盐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骨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拉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汤里,立刻屋里异香扑鼻。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
这是真正虔诚的吃,是饥饿年代的风景。
前些时候,有幸和阿城先生相会在北京,便要了一桌饭菜表示对他的敬意。他只是狠抽烟斗,象征性地拈了一点蔬菜。看来,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西双版纳的饥饿情结,几年西餐下来,人也发福了。
走进张贤亮的《绿化树》,吃的是面食。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锨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摄在滚烫的铁锨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锨,宛如一只平底锅,种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烟气,不到一分钟欢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地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
读到这,已经垂涎。
还有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
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回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古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
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一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宋健安慰说,没关系,还不够1斤呢。
实习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神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 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惟有一个馄饨摊孤独地支在街口。
卖馄饨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经营。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馄饨的抄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
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意思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得最好。
张嘴就有学问
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人膏肓还有人劝,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
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那时的海鲜是天价。
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
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
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动物保护协会设宴招待,端上了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
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比起来,“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盆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
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珠海,我们去录制澳门回归的节目,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大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有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来晚了,已经吃掉了。
如此吃法,又和动物有何区别?
1999 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的学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信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着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天津的徐建华认为:要想抓住儿子的心,先要抓住儿子的胃。
北京的徐慧玲说,自己嘴上有吃痦,最适合做这期节目。
沈阳的李福迅则说,下乡当知青时吃过瘟猪肉。
北京的陆晓黛说,老公做的“小雏鸡”,居然是实验用的小白鼠。
湖南李申玲的故事似曾相识,1962年,家里做面条,全家眼巴巴等着,面条出锅时,老师“恰巧”来家访,一口气吃了 6大碗。全家人尊敬老师,更心疼面条。
阿城说:“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这个理论,我实践过一回。好友小石约我去了韩国,在那儿,每天有朋友请我们吃烤肉。10天后,我终于没了食欲。小石拉我去了昂贵的中华料理,说是调理一下肠胃。哪知韩国的中华料理竟然和韩国料理毫无区别。一会儿,餐馆的老板走进来,一张嘴,并不会讲中国话,再一打听,虽是华裔,却从没到过中国。可见,他的中华料理只在理论意义上成立。
回到北京,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民工们围着饭菜你争我抢,一股酱香飘入我的鼻中,两眼开始扑簌簌地落泪。于是明白:树高千丈,根还是在萝卜白菜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