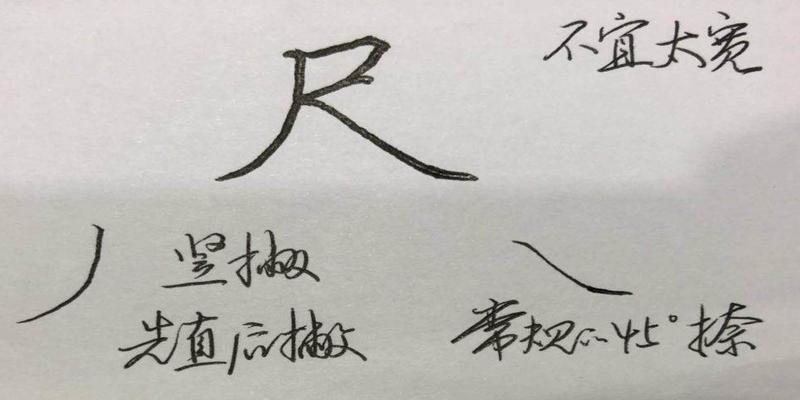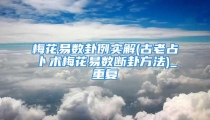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陈灿杰实习生常泽昱黄家樑躺上床,盯着天花板,许婉琪没意识到,眼泪已经不自觉打转,她不敢哭出声。婆婆摔伤在医院抢救时,心电图的光影,与那张陡然煞白的脸,不断在脑海中闪回,那一刻,她只怕丈夫回不来,见不到自己母亲最后一面。此前2021年3月,包括许婉琪丈夫陈庆路在内的5名河南劳工,远赴印尼务工,遭遇合同违约、护照扣押、工资克扣等多重困难。滞留工地近6个月后,五人铤而走险,试图偷渡至马来西亚后曲线回国,但很快在大马柔佛州因偷渡被捕,经由家属奔走、律师协助,马方最终决定不予起诉,直接启动遣返程序。此后,许婉琪开始了更为漫长的等待。除了婆婆的伤病,她有两个小孩等着照料,恰逢河南暴雨,她还得抽空回老家抢收花生,泥泞中赤着小腿,或蹲或跪,一颗颗地拔,拔到手生疼,全身僵硬。“像个陀螺,不停地在转”,可只有忙起来,她才得以从压抑中暂时抽离。按照预期,陈庆路1月14日乘机回国,结束3周隔离后,就能回到河南漯河老家,但他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显示阳性,赶在春节结束前团圆的希望再度搁置。截至发稿当天,历经遣返名额、批次、时间几经变动,高额机票无故取消,5名劳工中仅有魏朋杰一人回国。在不断攀升的债务、失去至亲的落寞、或是与丈夫的争吵、隔阂、分离中,留守在国内的劳工妻子们正备受煎熬。劳工所在的镍矿园施工现场。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1、赌两声枪响,窝在光板船里的魏朋杰彻底慌了。2021年9月18日,已近晚上10点,他在夜幕中紧忙跳船,奋力游向马来西亚柔佛州岸边,水深从胸口处点点褪去,临上岸,他才惊觉头顶站着两个军人。往哪跑?他蒙了,仅是往沙滩上一蹲,等人来抓。“左死右死都是死”,上船时,他只想赌一把。此前的3月,魏朋杰经工友介绍,到印尼做焊工。按外包公司的口头约定,一天500块工资,每月保底做27天,外加每月生活补贴1万,工期半年。该项目被工友称为“德龙三期”,主营不锈钢一体冶炼。至于合同,则商定到印尼后与项目外包公司签订。等开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直接绝望了”,天气暴晒,洗澡水是从土坑里抽的,透着一股臭味。更难忍的是,做工时想抽支烟,手头的活儿也不能停,否则,带班工头随时拍照,作为怠工证据,扣数百块工资。“人又不是机器!”魏朋杰说,厂区氛围压抑,他有个工友和带班闹矛盾,拿圆珠笔插了对方肚子,被群殴后用开水浇手。厂区外,保安持枪把守,还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劳工滞留。“(魏朋杰)去没几天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张娅杰说,她的丈夫魏朋杰初到印尼,有时也会聊工作的事,但他不想让家人担心,答应坚持做完。她也劝他忍着,反正只有半年。当时,张娅杰刚进江苏一家电子厂上班,患有心脏病的她则忍受着夜班“嘤嗡”的声响,总是心慌、失眠,她特意买了助眠保健品,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她和公婆还一直住着河南焦作农村的老屋,她想打工拼出个县城房子的“首付”,将来可以留给孩子。临周末,魏朋杰会提前让妻子把俩儿子聚一块儿,再到工地附近的信号塔下开视频。3岁的小儿子还不懂事,8岁的大儿子则会问他啥时回家,他只说快了快了,“10天半个月一直这样拖。”魏朋杰与2个儿子的合影到去年6月中旬,他和另外四个河南工友收到合同:工时延长,补贴骤减至一千:工期不定,短期内无法回国的话,要到其他工地干活。在魏朋杰眼中,这就是卖身契。5名工友与家属协商后,一致未签,要求辞职回国。但老板表示,每人交75000元才给安排。5名劳工收到的工程劳务合同书许婉琪回忆,原先报喜不报忧的丈夫陈庆路,听到这个数额,突然情绪爆发,哭着说出自己的遭遇,让她转告他父亲去借钱。当时许婉琪在县城一家儿童摄影馆做助理,每月两千多的工资,扣掉两个小孩零零散散的生活费,一年下来基本“没有落钱了”。家属筹钱期间,另一位2期工程老板声称回国只要5万,连夜包车将5人拉至300公里外的肯达里工区。5人交了钱,忍受着老鼠肆虐的宿舍、吃了2个月泡面,几乎吃吐。5名劳工公用一个小锅煮泡面吃5名劳工在二期工地住的宿舍眼见交了25万依旧回国未果,王兰不断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投诉,并找媒体爆料,要回了23.8万,但丈夫张强并未领情,他怕在当地遭到报复,“他就觉得我管得有点多。”王兰觉得,5人临偷渡阶段都非常敏感,随便问个话,“都觉得你是在套取他的信息,你会不会出卖他们”。魏朋杰也坦言,伴随压力增加,他对妻子的态度有时很“恶劣”。为着回家、乃至种种开销,他和妻子不知在微信吵了多少次,有时吵急眼了,他会带些难看的字眼,连着互相删好友、拉黑、冷战,而张娅杰只能打给他的工友帮忙传话。张娅杰说,丈夫提过偷渡,说能省点钱,被她一口回绝,“我说你想过孩子吗?”她让他走正常程序,后续花多少钱,她都想办法凑,他也答应了。可因护照始终被外包公司扣押着,他们最终选择了偷渡至马来西亚再乘机回国。蛇头是2期工区周边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偷渡费每人13000元。按照魏朋杰预期,登陆马来西亚后,穿过岸上的广阔森林,再幸运一点,他能在几小时山路中避开马来虎、云豹,找到接应蛇头,再给即将生日的母亲打个电话,说自己很快回家。可5人在登陆马来西亚后,多是原地蹲下,有人冲进林中,仍被抓了回来。前往警局路上,他们都不说话,魏朋杰能感觉到,大家心里似乎都在埋怨着什么,大概就是:“这下去球了(完了)。”2、离王兰回忆,张强偷渡前一晚,打来电话,让小女儿接听,说自己这次没挣着钱,没法给她买她要的那张公主床了。想多挣点,是他们出国时最简单的念头。2020年疫情封村,陈庆路基本待在老家河南漯河种地。去年3月,村里解封,他想去迪拜打工,无奈航班又因疫情停飞,他转而去了印尼。“劝也劝不下”,许婉琪说,当时县城一所不错的小学恰好招生,她小孩想读的话,得在那儿有房,夫妻俩为了凑首付,负债13万。陈庆路想过,等从印尼回来,就把这笔账给清了。魏朋杰说,疫情爆发后,国内工期不稳定,活少,他也没听妻子的话,执意去了印尼——家里开销紧张。而当他们出海时,别离、养家的辛酸,同样落在她们身上。自从丈夫情绪爆发,许婉琪每天都要给他消息,聊儿子,聊家里装修进度,试图调动他的情绪,只有收到丈夫回复,她才能安心入睡。丈夫被捕之后,她不知打了多少电话,发了多少微信,却没等到回复。她不知道,他的手机已坠入海中。她后来在王兰创建的印尼失联劳工家属群看到一张报道截图,是马媒《星洲日报》刊登的5人偷渡被警方逮捕的照片。她一下没认出丈夫来,照片有些糊,且与5人一同被捕的,还有10个印尼籍偷渡者。她把截图给自己两个小孩传阅,说玩个游戏,爸爸在玩躲猫猫,看谁能在人群里找到他,“他们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有关5人被警方逮捕的照片那时,因两个小孩接连感冒、发烧,加上婆婆的伤病,许婉琪只能选择辞职,每天在医院、学校、家三点一线跑着。一早起来,掐着时间给小孩领吊瓶,给婆婆送饭、清理排泄物,接小孩放学,再回医院……晚上独自开着电瓶车回家,她只觉恍惚,“闯红灯我都不知道。”张娅杰与丈夫失联后的第三天就坐上了辞职回家的高铁。路上,她也在群里看到了那张照片,“也不顾及(旁边)有人没人,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至少丈夫还活着,且不是落在蛇头手里,她赶忙给公婆打电话报了个平安。那天恰好是中秋节,也是婆婆生日,但家里都没有庆生。与二人相比,王兰的生活本来自如一些,她的工作能兼顾带娃。2014年生下女儿后,她办起晚托班,苦心经营,陆续收了80多个学生,每晚开车送学生回家。她从来不愿轻易放弃经济独立的可能,2017年生完二胎后,事业停滞,她举债加盟教培机构,从头做起。虽然丈夫张强常和她说,就算日薪只是多20块,他也愿意换一个地方打工。对他这次仓促前往印尼,王兰心里明白:丈夫觉得她的补习班做得还行,他却帮不上忙,加上他一些朋友又爱说些男人赚不到钱的风凉话,刺激了他。“他选择去的话,我尊重他的决定。”王兰说,张强收拾行李离开的那个早上,她躺床上装着没醒,他一开房门,她就闭眼,她知道拦也拦不住。她记得,临走前张强对她说了一句:“我以为你没醒呢。”她回,“我不想醒。”王兰一家合影3、执尽管王兰对张强出海表现“淡然”,但在他被捕后,她一直有个执念,只要自己不断付出,他肯定能第一个回家。去年9月19日凌晨,她收到丈夫被捕后发来的短信,“担心是有,恐慌没有,我会做起(事)来”,她开始打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报警、给张强留言。到早上八点,人完全失联。蛇头找过她,说再交2万,保证安全回来。她想走正常程序,直接拒绝了。因国内警方难以介入,又等不及12308回复,王兰隔天紧急联系朋友,委托马来西亚一家寻人机构找人,收到大概位置时,她两天没合眼了。其间,她同时联系着其他劳工家属,还需要陪她奶奶做手术,大脑在就医与寻人中来回切换。王兰说,确定5人被扣押在马来西亚北干那那移民局的扣留营,暂时没有人身危险后,她才稍感安心。当时,马来西亚华裔律师刘毅龙出于对出海劳工权益的关注,自发接手该案件,费用全免。王兰半夜梳理5人在印尼的前后遭遇,并将相关报道的背景、截图、照片一一备注,打包发送给律师。此外,她坚持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写邮件。王兰坦言,自从帮5人要回那23.8万,受到张强指责,她心底总有顾虑,怕又“做错”什么,可尽管两人关系已变得紧张,她还是怕他在外边受罪,“我对他还是有爱的。”2期工程老板退回23.8万,称剩余1.2万抵扣为5名劳工的生活费而更大的波折,还在后头。去年11月17日,王兰通过票代抢到5张厦门航空的机票,一张28000,预定12月3日回国。票号和行程档案发给大使馆后,隔天下午收到回复:根据防疫要求,每所移民局扣留营只能安排每趟航班最多4名人员遣送回国。这一下,家属群中免不了争论,张娅杰说,回了4个,剩1个咋办?他要是心里压力太大寻短见呢?大使馆工作人员给王兰的邮件回复,称家属可安排其他从马来西亚直飞回国的航班厦航11月18日发给律师刘毅龙的邮件表示,由于马来西亚疫情及厦航总部无法接受以上5人乘机,5人可办理全额退票。厦航运送5名劳工的相关要求厦航拒载后,张娅杰在网上搜了各种求助电话,闷在房间一打就是好几小时。她梦过好几回丈夫回家,她和平时一样在家洗衣做饭,突然间就看到他回来,“冲过去抱着他哭,娃娃(也)在那哭。”可每一次,梦都在这里戛然而止。张娅杰记得第一次接到丈夫在扣留营打来的电话时,他慌张而紧迫,像要赶在挂断前问完所有问题,她也仓促答着,3分钟不到,电话挂了,她还有好多话积在心里,“就感觉这个声音听一次真的好难啊。”王兰也没闲着,她联系票代抢其他航空公司的票,又求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去厦航吉隆坡办事处帮忙询问。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与厦航沟通,厦航最终同意运送5人。但每次登机不能超过2个,分为3个批次:2021年的12月24日、2022年1月14日、2月4日。几乎每个人都想让自己丈夫最早回来,还想过抓阄,争执不下,干脆交由律师决定。魏朋杰成了其中第一个回国的人。魏朋杰在移民局拘留营做体检刘毅龙解释,魏朋杰先回来,是因为他健康问题比较迫切。他同时表示,接手本案最大的难点,在于“使馆和航司针对返华人员(5名劳工)的防疫规定一直存在差异”。例如,针对曾经确诊劳工,航空公司要求对方必须在康复3个月后,才能重新根据使馆指定的防疫程序返华,但他从大使馆得到的讯息,是康复2周后即可启动相关程序。以及,使馆或航司也未直接解释何谓“康复”,“要做多少检测?什么样的检测才算康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个别向使馆查询才能得到答案的。”得知第一个回国的不是自己,张强无法接受,与王兰吵到不欢而散。很快,他又来道歉,她没吭声,只说了句,“我尽力了”,不过在梦中,她仍和张强吵着,被责怪着,醒来便难以再入眠。确定魏朋杰第一个回来后,妻子张娅杰给他打电话,但他心里始终不放心。魏朋杰回忆,去年12月3日航班取消那天,他一早坐牢门前等着警官叫号,等到快中午,知道没戏了,直接往地板一躺,不想动了。扣留营60平米不到,最多时挤了81人,“就那么大个笼子”,他在里边总是饿得发慌,瞪着眼看天花板,想起母亲烧的西红柿鸡蛋面非常好吃,越想越饿。但他想得最多的,是搞个绳子上吊算了,“你要拿个刀一下子,真有这个勇气敢去自杀。”不过念及家人,他又下不了决心。“他要的答案我没有”,张娅杰无助又忐忑,不到丈夫坐上飞机那一刻,她只能战战兢兢地过着。4、抑扣留营外,因丈夫们的集体“缺席”,她们自身的情绪也在压抑着。张娅杰说,与婆婆解释魏朋杰的回国进程尤为困难,对方不理解,脾气又急,总让自己去催这催那,像被厦航拒载,她成天在家絮叨。自己说多了也烦,但冷静后,还得说到对方听懂为止。邻居问起丈夫的事。她搪塞几句了事。“忍着连闺蜜在内谁也不说”,和朋友出门,被问到怎么总是在看手机回消息,她就故作轻松,笑着不说话。在这期间,她已被诊断为轻度抑郁。多少给她一点慰藉的,是两个孩子。她一到家,他们就很开心,又要亲又要抱。有时她正心烦,两人还闹的话,她真的感觉要疯掉,“我心里边压得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入睡后,才是真正的消停,可她又觉得,太安静,夜变得长了,心里反而不好受。她不敢去想和他的过去,“现在就感觉你不(被)允许去回忆。”“感觉好像天塌”,张娅杰说,心烦她就出门兜,或者在家打扫卫生,让自己忙起来。自从丈夫被捕,她也开始喝点酒。对许婉琪而言,雪上加霜的是谣言中伤。去年11月中旬,老家开始传他丈夫没回来,是因得传染病被关了。有些人碰着她家小孩,甚至故意去问:你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提及此事,她有些哽咽,她说被街坊邻居问到丈夫的事,她的心理防线会直接崩塌,她两个小孩其实一直不知道爸爸出事了。“如果可以的话,谁愿意让自己的老公出去?”许婉琪说,她满脑子想着怎样让丈夫回家。有次她和小孩站在桥上,想着要是能换他瞬间回来,“哪怕我带着小孩子从桥里面跳下去都行。”许婉琪2015年生下大女儿后得过严重的产后抑郁,容易钻牛角尖。陈庆路在印尼的很多遭遇,反倒是公婆瞒不住才告诉她的。面对丈夫回国的波折,她感觉“脑壳都要炸开了”。其间,她婆婆因摔伤胆囊炎加剧入院手术,所幸没有性命之虞。婆婆怕她多想,没敢提儿子的事,只是住院时偷偷翻着手机里的照片,自言自语叫着他的名字。有好几次婆婆让她回家带小孩,实在憋不住了,才给她打电话,她又骑上电瓶车匆匆往医院赶。“天天都是神情恍惚的”,许婉琪想要宣泄,只能躲房间悄声地哭。每次和丈夫打电话,她会说家里都挺好。同许婉琪一样,无论碰到多大变故,王兰都不愿轻易诉说。去年10月,她的继母因肝腹水去世,她还想着,如果张强先回来,他至少能在丧事上露一面,那她心里能有个安慰,“至少不会让人看笑话”——按当地风俗,本该是男的领丧,现在得她来做。王兰同时提到,继母的离去还给患有心脏病的父亲巨大打击。原先,他会帮自己带下小孩,现在父亲过得浑浑噩噩,早上睡觉,下午打牌,晚上喝酒。恰逢她也遇到事业危机,伴随“双减”政策落地,她的教培公司直接停摆。那时她最怕朋友突然关心她,哪怕只是简单一句问候,她都觉得自己会崩溃,她只能在心底默念,“我会熬过去的,太阳升起来就会好的。”而家中的变化,除非已成定局,王兰才会和丈夫提起,她清楚,和远在他乡的男人说这些意义不大,“何必徒增伤悲呢?”5、盼历经波折,去年12月24日,魏朋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那天已经通知航班晚点了,他愣是站登机口前等着。乘务劝他去座位上等,他怕这么一等就被撂下了。当时他穿着防护服,闷得满头汗,怕查体温过不了,赶紧把帽子给摘了。临起飞,飞机又出了故障,全员下机,他一下慌了,空姐给他发饭也吃不下,“起飞之后我才吃的饭,心里才带劲。”飞机一落地,他感觉“脸上都冒出了个微笑”。到宾馆隔离时,魏朋杰和10岁的大儿子打视频电话,以前儿子基本不搭理自己,这次一见面,儿子就掉泪了。魏朋杰说,和妻子打电话时,儿子常在跟前听着,装着不说不问,但其实“心里都知道”。在扣留营,魏朋杰也反思过,自己总惹妻子生气,甚至医生都说过她的病和总生闷气有关。他回忆,2015年开驾校时,他“赚点钱有点飘了”,天天不着家,没少和她吵架。她也强势,打架打不过,脸要给他掐了,大着肚子都要拿只拖鞋追着他打。后来驾校亏损。他没钱还,被告上法庭,她赶忙借钱在庭上把人赎了出来。“每次我出事,她都是冲到最前面。”对这段婚姻,张娅杰也后悔过。她初二辍学打工,18岁意外怀孕,知道身孕的20天后她和魏朋杰领证结婚,“其实也有落差”。和闺蜜闲聊,她也抱怨过自己咋就嫁得那么差,“但想想这是你的命,你没办法。”张娅杰说,2019年生二胎时,丈夫算成熟了些,当时他正在迪拜打工,提前回家陪产,给她做饭、洗脚、帮忙带娃。但二人间的关系,张娅杰也不知怎么形容,说是亲情,好像有点肉麻;说是爱情,结婚十年还谈这个,又不太现实。她就想着,这次等他回家,先让他在家补补身子,之后,日子照常:挣钱、还账。算上他偷渡、机票、隔离等开销,她家借了将近9万。“有个人回来,就有盼头,哪怕借得再多”,因这场意外,许婉琪家里同样负债累累,但丈夫回国前,她一直给他打气,说拼个两三年,总归能把账清了。她现在担心疫情加重,又会封村。许婉琪说,跟丈夫待在一起就让她挺有安全感的。她是单亲家庭,初中毕业后进厂工作了几年,到点上下班,不爱往其他地方跑。2012年,19岁的她通过相亲认识丈夫,挺合得来,很快结了婚。“我就是按部就班的人”,但婚后的独自带娃的压力,加上丈夫不太往家里寄钱,她过得有些窘迫,“我口袋里面有一块钱,就紧着这一块钱去花。”种种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她只觉给丈夫生的小孩,像生了个玩具,他打工回来,“看着、抱着这个玩具挺好的”,却不知道小孩闹了、哭了、饿了是个什么状况。带娃5个月,她想过自杀,甚至给母亲写了遗书。隔年,她意外怀孕,候产时把丈夫叫了出去,“我疼我自己忍着就行了”。小孩子抱出来时,手术室门没关,他看到喷了白褂子的一身血,吓得说话都发抖,等躺在床上的她被推出来,她笑了下,安慰他不要哭。许婉琪说,应该就是那时起,丈夫才有动力去上班,知道给家里挣钱了。“平平淡淡的这样子就好了”,许婉琪说,除了去年,每到结婚纪念日,他在家的话,都会做上满满一桌子菜,要是在外边赶不回来,也会订一束花。王兰说,她曾经也憧憬着“有人与我共黄昏”的婚姻,但婚后,她很快发现张强更习惯和人出去喝酒、三更半夜回家的生活。两人但凡为此吵架,他就外出打工,回来以后,“死循环一样”,他继续要玩,她还是会吵。她觉得好像跳进了一个坑里,却没人拉她一把。但这次进了扣留营,张强似乎发觉了王兰的不易,总说她在家辛苦了。等他回来,以后一定好好过。听到这,王兰会直接打断,她讨厌画饼,“一路走来,饼不好吃,也没有吃到过。”在国内承受着种种变故的日子里,王兰愈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人也可以。当初相亲仓促迈入婚姻的脚步,显然太不理智了,以前就那么熬着,但距离变远、时间拉长,“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不了”,如果他回来还是没变,她不愿再妥协,“他还想飞,那我就放了他。”她想给自己两个女儿树立一个榜样,任何时候,都不要做手心朝上(编注:意为索取)的人。补习班受到重挫后,她转而报了个美妆班,等学成后,她想开个小店。每次去上课,下了公交车,她都会一路小跑,只觉得激动,好像真的在和时间赛跑。“我好久没这种感觉了,那种从头再来的感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许婉琪、陈庆路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许振华对本文亦有贡献。)责任编辑:彭玮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