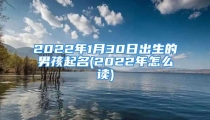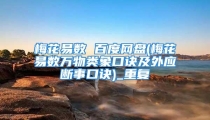肖馥莲(复旦大学)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主办,主持人复旦大学高晞教授谈到创办本系列讲座的初衷,一、医学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已不再是史学研究的新热点,自本世纪初,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同仁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到医学知识、疾病史和公共卫生史,经二十年余年的积累,医学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受到业界学者的广泛的重视,推进了该学科的发展。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进入到该研究领域,我们发现目前国内缺乏与之相应学科培养的机制,该学科始终处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中间地带,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和成熟的理念体系。海外研究机构和学院有着成熟而系统的培养体系,医学史研究包括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积累。近年海外学者包括一些在海外接受教育中国青年学者,已有不少成果呈现。因而考虑邀请海外优秀学者对国内从事医学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对医学史有兴趣学生讲授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以期拓展视野,了解域外研究的动向。三、2020年以来的疫情虽然阻隔国家间的学术交流,看上去似乎有全球化终止的迹象。但是人类无法捕捉病毒,以其迅雷不及耳的速度在全球传播,其结果实为学术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契机,一方面为疾病史的研究和为思考如何应对疫情带来新的视角和路径,使医学史学者能够感同身受地去理解全球化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疫情导致的阻隔开启一个新学术交流空间,线上平台成为学术交流的常态,反而刺激了全球性的交流。从这个层面讲,这样的学术交流方式为学术全球化开创一个新的前景。基于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计划邀请国际学术界中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杰出的或有代表性的十位学者,在一年时间里陆续推出,介绍他们在中国医学史中的最新议题和最新成果,以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解释他们的研究源起、采纳和应用的史料、问题意识,分享他们如何展开研究的方法、思路以及采纳的理论。该系列以线上的方式向国内学者开放,并邀请相关的学者与专家与演讲者展开深度对谈,以拓展演讲的层次和外延。通过空间网络上面对面的方式,让国内的学者直接了解海外中国医学史学家的近况和医学史研究的新方向。本演讲系列第一讲由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担任。梁其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就开始投入到医学史的研究中,并一直是医学史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年轻的研究者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希望,并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来。梁其姿将她自身海外求学所得和自己研究的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来,同时,她还将中国学界的研究近况和青年学者介绍到世界上,与国际学者进行广泛而深入合作交流,在世界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难能可贵的是,长期以来,梁其姿积极支持与关怀中国的青年学者,先后培养了诸多学生。2021年10月2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第一场在线上举行。主题:域外(西方)中国医学史研究新方向:食物与药物。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为与谈人,陈明的究领域包括印度语言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近年来,他在医学文化史的领域发表了诸多文章和出版作品,代表作包括《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梁其姿与陈明合作发表过探讨作为物和知识的阿魏是如何在全球流转的学术论文“TheItineraryofHing/Awei/AsafetidaacrossEurasia,400-1800”(inEntangledItineraries:Materials,Practices,andKnowledgesacrossEurasia,ed.PamelaSmith,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19)引言:物的历史——物作为知识建构秘码的黑盒子物的历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物作为知识建构密码的一个“黑盒子”(blackbox)隐含了丰富的内容。物中包括技术面、制度面、人与物的关系,也隐含着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概念。药物跟食物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性和思想性的问题,通过解构这些物就能看到其中交错复杂的内涵,因此称它为“黑盒子”。两年前,我和高彦颐(DorothyKo)、薛凤(DagmarSch?fer)在北大开设物质文化史课程,课程内容就包括对物质文化的内容进行解构。近年来我关注的是“食物与药物的问题”,思考的有这几个方向,首先是中国传统食物药物中食疗本草的概念。第二部分是西方学界中有关传统中国医疗文化史中食物和药物的研究的抬头。早前,西方学界对中国医疗文化史的研究基本围绕着观念的历史,比如“五运六气”、身体观等观念性的讨论。近年来,西方学界从“物”的角度研究中国医疗文化史有新的发展。第三部分是近年西方有关中国疾病史、身体史、环境史等研究往“食物”史的一个转向。物是隐藏知识建构密码的黑盒子,人们怎样才能通过解构物去了解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了解物是什么?首先,物是一个技术体系(technologicalsystem),物是透过技术介入才能够成形。了解物的历史需要了解这个物的技术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用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在历史上有何变化?高彦颐新作TheSocialLifeofInkstones:ArtisansandScholarsinEarlyQing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7)就是关于物的历史很好的研究,书中高彦颐探究了砚台是如何从一块石头变成一个砚台,这其中技术是如何产生和进入的。其次,物不只是一个技术,它也有社会性,即物也是一个社会技术体系(sociotechnicalsystem)。荷兰技术史学者WiebeBijker研究西方自行车的构成过程,自行车的结构与外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相关研究包括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icalSystems:NewDirectionsintheSociologyandHistoryofTechnology,London&Cambridge,MA:MITPress,1987;OfBicycles,Bakelites,andBulbs:TowardaTheoryofSociotechnicalChange,London&Cambridge,MA:MITPress,1997)。这些变化与社会改变密切相关,骑车的人从男人扩展到女人和小孩,不同阶层的使用者、不同环境的使用需求被纳入自行车设计的考量因素。因此,车的技术变化是随着社会與使用者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实物的形成也是社会宇宙观与技术相辅相成的结果,它是社会技术与世界观一个交错。食物与药物的主题就与之相关,但食物药物与砚台和自行车也有不同,吃进身体的药物食物与环境是什么关系?身体跟整个宇宙和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对食物药物的使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学者西敏司(SidneyMintz)作品《甜与权力》(SweetnessandPower:ThePlaceofSugarinModernHistory,NewYork:VikingPenguin,1985)中讲述了糖是如何从贵族食物变成劳动阶级的食物,这与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本书涉及物的政治史、技术史和社会文化史,是解构“物”的经典作。陈寅恪先生曾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在此借用这个说法——“解释一个物也是做一部文化史”。一、中国传统食物与药物的模糊界线:食疗本草的传统英国学者罗维前(VivienneLo)曾在2005年发表论文“Pleasure,Prohibition,andPain:FoodandMedicineinTraditionalChina”(inOfTripodandPalate:Food,Politics,andReligioninTraditionalChina,ed.RoelSterckx,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5),该文强调了食物、药物在传统中医中的微妙关系。文中提到食物与药物中间模糊的界限早已出现,唐代孙思邈(541-682)的《千金方》中就有《食治》卷,“食治”即用食物来治疗。《食治》中言:“夫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滥亦然。”医生在了解病因后应该先用食物治疗病人,效果不好再用药。因为药性刚烈的,容易治坏病人,用药失当会伤害病人,滥用药物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说,食物跟药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马继兴对食疗传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他早期关于文献学作品《中医文献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中讨论到食疗传统的。他在书中提出食疗传统的两个关键时期:唐代和明代。唐代已有本草食疗的概念,唐代第一本食疗的书是孙思邈的学生孟诜(621-713)所著的《食疗本草》。这本书虽已失传,诸多内容在后世本草典籍中仍保存着,如宋代的《证类本草》。以枸杞为例,《证类本草》卷12言:“枸杞(寒):无毒。叶及子:并坚筋能老,除风,补益筋骨,能益人,去虚劳。”可见,枸杞虽为食物但文献也会提及它的治疗功用。明代后期卢和(生卒年不详)的《食物本草》(两个版本)中将食物分为“水、谷、菜、果、禽、兽、魚、味”八种,此书在明末流传较广,高濂(生卒年不详)的养生专著《遵生八笺》也在此时较为风靡。这说明养生的实践与观念在明代达到了一个巅峰,这跟食疗的发展很密切关系。唐代医者已经主张食疗为先,到了明代,吃好的食物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养生实践。明末出版的《本草纲目》中也提到很多食物,罗维前就曾认为李时珍(1518-1593)是个美食家,《本草纲目》也是一本食谱。以酱油为例,《本草纲目》中载有制作酱油的原料豆豉,“豉,诸大豆皆可为之,以黑豆者入药。有淡豉、咸豉,治病多用淡豉汁及咸者其中心者……”还包括酱油的制作方式,“造豉汁法:十月至正月,用好豉三斗,清麻油熬令烟断,以一升拌豉蒸过,摊冷晒干,拌再蒸,凡三遍以白盐一斗捣和,以汤橘丝同煎,三分减一,贮于不津器中,香美绝胜也。有麸豉、瓜豉、酱豉诸品皆可为之,但充食品,不入药用也”。李时珍讲到豆豉除了入药之外也是一种美味的食物。罗维前目前正进行中国医疗史中“营养(nutrition)”观念的历史。19世纪以后,西方“营养”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它包括了维他命、蛋白质等西方生化学的概念。但是中国食疗的传统里有一套独特的对食物评价的体系,很难直接用西方的营养概念来诠释,罗维前老师如何把中国食疗的观念翻译为nutrition,我很感兴趣,很期待这本书的出版。二、传统中国医疗文化史研究领域里食/药物研究的抬头(materialturn)西方学界对中国医疗史往药物研究转向的几部代表性新作,他们的研究视角都是从以往身体观的历史转到从物的角度来看待医学、身体和疾病。第一本作品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刘焱的新作《以毒为药》(HealingwithPoison:PotentMedicinesinMedieval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21)。本书讲述了汉代到唐代,药物中“毒”这一概念的形成,以及中古以前药物的毒性是如何被建构的。书中的“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poison”,而是指药物中一个系统的性质。毒性强说明该药有比较热,它比较厚等某一方面强烈的性质。这些含毒性的药物可以处理一些棘手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后遗症。刘焱的研究梳理了从汉代的本草书一直到隋唐的本草书,他发现早期的本草书含有差不多500多种本草的药物,基本上22%是有含毒性的。有毒性的药物虽然是有疗效,但当时医生的却将这类药物放置在较低的等级中,意思是有同类型药物时,不会优先选用含毒性的药物。这也能反映出古代医生和用药的人的宇宙观即:小心用药。其实早在1997年,法国学者奥宾尔亚(FrédéricObringer)就出版了一本关于毒性药物的研究L'aconitetl'opriment:DroguesetpoisonsenChineancienneetmédiévale(Paris:Fayard,1997)一书。书中对“附子”进行了集中讨论,引用了诸多巢元方(605-615)《诸病源候论》中关于毒药的观点。对比来看,刘焱的作品比较则是从一个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药物里面“毒”这一概念的形成。刘焱此书集中在隋唐及以前的带毒性的药物上。它在讨论药物毒性的时候,也提到社会性的问题。首先,早期建构毒性概念的医者基本上都是有道教背景或者贵族背景。透过道教的内丹实践,他们具备深厚的关于药物毒性的知识。第二,这些医者很多都是从西北方来的,具有区域性的特色。第三,解释了药的毒性建构,即药的性、气、味是怎样的?最后是如何使用毒药。总结而言,刘焱此书将把药物里毒性问题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产生?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产生?”提出了一个宏观全面的看法,是中国中古时代医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著作。第二本书是去年出版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边和的新作《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KnowYourRemedies:PharmacyandCultureinEarlyModernChin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20),这本书讲述明清药物知识建构的变化。边和认为明清时期医药知识分家,所谓医药分家,就是医生虽仍拥有治疗的知识的本领,但已渐渐不能完全控制药物的知识建构。医生失去了垄断药物知识的权利,很多其他因素已经介入药物知识的建构中来。很多药商成为药物知识的建构者,尤其是具有士人背景的商人。在明清药物市场的形成中,药物成为商品,商人也就随之介入。商人知道药物产地和价格,商人再将其卖给其他人,知识建构就落在不同人的手里。边和书中也谈到清代市镇药肆经济,清代著名的药店如“同仁堂”这些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药肆经济的形成也是药物商品化的重要指标。随着药物市场的形成,药物来源渐趋多元化。人们开始追求“道地”药材,即关注哪个地方所产的药物最好,人们普遍都不喜欢种植的药,认为野生的药材才有药力等等。这一时期追求“道地”药材在明清药肆里变得很重要,这是在隋唐时候仍没有出现的。追求“道地”的概念也与地方知识相关。特别是在《本草纲目》出版以后,很多有关本草的书提到地方的药物出采。边和书中特别提到,清代医家赵学敏(约1719-1805)的《本草纲目拾遗10卷》就体现了地方药物知识在《本草纲目》里的重要性。以我最近关注的酱油研究为例,《本草纲目》中记载:“以面豆拌罨成黄,盐水渍成之。伏造者味浓,秋油则味薄,陈久者入药良。”秋油是江南地方的酱油,不是全国性的用法。诸如此类,赵学敏在书中举出很多地方性的药物来说明这些药物或者是食物的特性,比如“味咸性冷,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涂汤火伤,多食发嗽作渴”。他认为酱油糟油可以杀毒,也可以治疗这个烫伤,这些都是地方知识的收集。明代以后,药物知识增添了一份地方性知识在其中。梁老师举例道,明清之交,在广东有明遗民在佛山南海地区(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进行药物田野调查与收集,把当地可作食物或药物的植物资料记录下来,这类的书籍在清代日渐增多。这也说明药物的知识已经不集中在中原地区或者是由几个著名的医家控制,而是比较分散。第三个例子是我曾与陈明老师合作过关于阿魏的研究“TheItineraryofHing/Awei/AsafetidaacrossEurasia,400-1800”(inEntangledItineraries:Materials,Practices,andKnowledgesacrossEurasia,ed.PamelaSmith,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19)。阿魏的拉丁文是Asafoetida,意为一种很臭的药物。阿魏原产于西亚,是由一种植物根部的一种脂液形成的。欧洲人很重视这个药物,认为它很有效,但是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个药物从何而来。17世纪,德国医学家刚伯法(EngelbertKaempfer,1651-1716)前往波斯进行田野调查,并记录了当地人采集这个树脂的过程,并将这个植物的枝叶形态绘制下来。其实阿魏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但是中国人从未看过这个植物的具体形态。到了宋代,当时中国人听说阿魏来自这种植物的根部,但却不知道这个植物具体是怎样的。所以在宋代广州阿魏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本草绘者只是随便画一个树的样子,在根部再着墨一下,画出心目中的阿魏树。德国学者通过田野实践给欧洲读者带来关于阿魏的知识,但在中国,人们只知道阿魏具杀虫除臭助消化的功用,但对这个植物知识却很模糊。由此可以看出,阿魏这个来自西亚的植物,在欧洲产生一种知识,但是在中国却是产生了另外一种知识。唐代至清中期,中国本土没有出产阿魏的药物知识建构。早期阿魏进入中国时,人们虽不清楚其植物是怎样的,但在正常使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描述阿魏道:“味辛,温,无毒。主杀诸虫,去臭气,破症瘕,下恶氣邪鬼蛊毒。生西蕃及崑崙。”孙思邈把它定性为温,是无毒的,可以杀虫驱恶气,并指出它不是中国本土的药,它来自于西域。到了明代,阿魏的药性还是维持着原来无毒温和的描述。《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还记载道阿魏“番人以作食料”。唐代的佛经就已经记载西域人将阿魏当作食物,而不是药物。宋代以来,阿魏主要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进入中国,因海运船只多在广州上岸,因此叫这种药物也被成为“广州阿魏”。宋代赵汝适(1170-1231)《诸蕃志》卷下“志物”中的“阿魏”条记载了一个神奇的传说:“阿魏出大食木俱兰。……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阿魏时,击羊于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于羊,羊毙,即以羊之腐为阿魏”。传说可见,人们知道阿魏为外来药物,但认为其具有毒性。传言采阿魏时需要将羊系在树下面,然后远距离将羊射杀。这样树上毒汁就掉进羊的身体里,羊的肉就成了这种药物。今天我们看来这就是假消息,但是这个假消息却充斥着市场,比如1885年的《本草纲目》上依旧沿用的这个插图,向读者传递着阿魏是毒羊肉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到明代的主流本草书籍都说阿魏是无毒的,但是宋代开始的插图就好像说阿魏是有毒的。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药物知识不只是纯粹掌握在医生的手上,也掌握在药商的手上。如今中国药店很难购买到阿魏,店家会以阿魏有毒为由拒绝买的普通客人。但阿魏作为食物是印度人在制作咖喱的时必不可少的原料。西方人认为阿魏很臭,因此叫它“魔鬼的粪便”(devil'sdung)。关于清中后期中国药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我已经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刘小朦的博士论文就是关注靠近农业区的药肆,尤其是药物知识建构参与者包括不同地方的采药者、种药者、制药者(炮制者)、卖药者,医者进一步脱离药物知识的建构,地方药理知识抬头。三、近代中国疾病史、身体史、环境史往“食物”史的转向有关中国食物史的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出现。早在1977年,张光直主编的关于饮食史的书籍FoodinChineseCultural:Anthropolog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YaleUniversityPress,1977)中就收录了诸多名家关于饮食的作品。这本书以朝代分章,从商代一直到民国时期。这本经典的有关中国食物史的论文集中包括从考古研究来看中国古代的人用什么器具吃饭,用什么仪式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是怎么的安排。此外还包括宗教仪式,祖先的食物与常人的食物有何不同?食物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重要的解释的力量,但这本书中谈到食物与健康的关系较少。1988年,E.N.Anderson的TheFoodofChina(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YaleUniversityPress,1990)一书中最后一章“FoodinSociety”中提到食物的药性,包括气、阴阳五行、寒热等,指出食物具有药物一样的功能。近年来,不少关于食物与健康的书相继出版。2018年,傅家倩(FuJia-chen)作品TheOtherMilk:ReinventingSoyinRepublican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8)以豆奶的历史为例,讲述了食物与现代国民健康的关系。豆奶在现代中国非常重要,这与西方蛋白质观念的输入密切相关。20世纪初,西方人的蛋白质基本上是从动物里面来的,但是中国百姓的食物里动物的占比较低。孙中山(1866-1925)就提倡中国人应该大量用黄豆来制造食物,因为黄豆里有非常充分的蛋白质。孙中山还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发展畜牧业以制作为食物,因为这太昂贵,而是应该集中在种黄豆,用黄豆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这个例子是西方营养观念进入中国后发生的有趣的变化,除了豆奶还有豆腐等,成为当时革命家推动的救国食物。另外一本书是我和美国学者MelissaL.Caldwell所编的MoralFoods:TheConstructionofNutritionandHealthinModernAsi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19)。本书主要讲述了整个亚洲的近代史里食物健康知识的再建构,讲中国方面有几篇文章。一篇是刘士永研究的战争期间营养问题,一篇是张乐翔讲述的茶与健康观念,还有我自己研究的素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蒋熙德(VolkerScheid)的近代中国养生疗法的全球化,他认为养生疗法具有哲学性,清末的养生其实受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影响。HilarySmith研究的乳糖不耐的中国身体,也是与蛋白质有关的问题,她提出当时中国一方面重视从牛乳吸取蛋白质,但很多人却对牛奶敏感,造成一种矛盾。MoralFoods一书基本上是讨论西方营养观健康观进来中国之后对中国饮食物文化的冲击。另一本我与中山和泉(IzumiNakayama)编的Gender,Health,andHistoryinModernEastAsia(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18)中也有关于身体与食物相关的论文。雷祥麟以台湾地区著名食疗养生专家庄淑旂的养生保健知识为切入点,看她怎样塑造这种风靡台湾的养生观念,又是如何去制作养生食物,教导人们怎样做运动。这些都是结合的不同传统的一种处理身体的近代养生法,食物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还有我对中国近代脚气病观念问题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到达亚洲后发现一种病叫“beriberi”,后来中国人将其译成“脚气病”。但在中国,脚气病这个名词在唐代孙思邈时就已经有了,这个“beriberi”与古代脚气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概念。欧洲人在亚洲观察到这个“新病”,认为吃米的亚洲人很容易患上这个脚气病,因为碾过的白米缺乏维生素B1。因此他们治疗亚洲人beriberi的办法是让病人多摄入豆、奶、肉等,让他们得到足够的维他命,后来就直接用注射硫胺作为疗法。但传统中国医学里的脚气病与地气湿气有关,不是食物的关系,因此用药就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医生曾超然在香港给病人治疗脚气病时就用槟榔来治,因为槟榔产自脚气病特别多的湿热南方,对这个地方病特别有疗效。香港一些译者把他这个方法介绍给那里的西医,因为这些西医在来亚洲之前没见过这个病。以脚气病为例,可以看出西方的观念进来亚洲之后,对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的冲击。HilarySmith的ForgottenDisease:IllnessesTransformedinChineseMedicin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7)一书也是讲脚气的,作者谈到西方维他命观念进来后对亚洲传统疾病观的一种扭曲,这个扭曲其实也甚至影响了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李约瑟鲁桂珍(LuGwei-Djen,1904-1991)在1950年代发表过一篇关于脚气的文章,就是完全是被西方的营养观带着走,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中早已有现代的营养学观念与知识,这实际是对中国传统脚气病观的一种误读。最后一本书是冯珠娣(J.Farquhar)2002年出版的《中国的食、色与健康》(Appetites:FoodandSexinPost-SocialistChina,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Books,2002),她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谈中国养生的观念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后,食、色与健康的一个关系。2002年左右是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得十分迅速的时代,那时讲究养生的多为商人和男性。这些人希望把自己补养得健康强壮,以符合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社会地位与角色。但是对养生知识的这样一个解释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养生观念应该是什么?是否会有新的养生观念出来,我们拭目以待。四、物相关研究的补充拓展与答疑作为与谈学者,北京大学陈明教授进一步补充介绍一些与“物”相关的研究成果。第一本书是2017年AnyaH.King的ScentfromtheGardenofParadise:MuskandtheMedievalIslamicWorld(Leiden:Brill,2017),这本书是关于伊斯兰世界麝香文化史的研究。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很多医学著作和本草书中在谈到麝香时会提到西藏,因为西藏也是麝香的产地之一。这本书还讲到麝香向西的传播之前的历史,包括麝香在香水和医药中的作用,以及麝香在西亚当地的宗教象征意义。第二本是2016年出版的由AnnaAkasoy,CharlesBurnettandRonitYoeli-Tlalim主编的论文集IslamandTibet:InteractionsAlongtheMuskRoutes,RonitYoeli-Tlalim(NewYork:Routledge,2016)主要研究西藏医学,她发现了伊斯兰世界和西藏的关系是沿着麝香之路的一个广泛的交流,但实际上这本书关于医学的内容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涉及到地理地图、艺术史、科学文学传记、考古,还有人类学的内容,此外本书中麝香与喜马拉雅山周边的贸易、文学的交流也值得一看。RonitYoeli-Tlalim今年出了一个新书尝试对医学史的重新定位,ReOrientingHistoriesofMedicine:EncountersalongtheSilkRoads(London,etc.:BloomsburyAcademic,2021)这本书主要研究范围是前现代东亚的医学史,Ronit运用到的资料包括了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的、库车(今新疆省库车市)的和开罗(Cairo,今埃及首都)的等,讲述了从敦煌往西,丝绸之路上医学的相遇,讨论了在中亚接触地带,术数和医学的交流。这本书中有一文与中医直接相关“Myrobalans:TheMakingofaEurasianPanacea”,文章讨论了三个诃子在从西边往东方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万能药的经过。佛经中就有记载诃子为“药之王”,但万能药的概念在中医中并没有形成,因此诃子没有像印度医学那样有那么高的地位。第四本研究是关于食疗的,PaulBuell与EugeneN.Anderson合译的ASoupfortheQan:ChineseDietaryMedicineoftheMongolEraAsSeeninHuSihui'sYinshanZhengyao(Leiden:Brill,2010),此书为《饮膳正要》的英译版和注释。《饮膳正要》在元代是跨民族、跨文化的、跨语言的饮食文化交流著作。EugeneN.Anderson正在翻译《回回药方》,《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都是我们了解中国人如何接受的伊斯兰医学的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两部值得关注的作品:一本书是也是关于中世纪地中海地区饮食文化史的著作PaulinaB.Lewicka的FoodandFoodwaysofMedievalCairenes:AspectsofLifeinanIslamicMetropolisoftheEasternMediterranean(Leiden:Brill,2011)。另一本是NawalNasrallah的厨房手册,AnnalsoftheCaliphs'Kitchens:IbnSayyāralWarrāq'sTenth-CenturyBaghdadiCookbook(Leiden:Brill,2014),这是一本关于厨房的著作,书中对于食物的配方、制作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如关于西瓜这个词的不同名称和解释。这些书籍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的食物史和药物史提供背景层面的意义。陈明补充了港澳两地和台湾地区今年关于食物和药物单个的研究。林富士研究槟榔与药物和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关系。林富士还主编了《红唇与黑齿:槟榔文化特展展览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手册。(林富士关于槟榔的研究还包括:《槟榔与佛教:以汉文文献为主的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7,第88卷第3期;《中国隋唐五代时期的槟榔文化》,《新史学》,2018年,第27卷第2期。)张哲嘉讨论大黄在鸦片战争前后与西方的关系,他还写过日本对于大黄知识的认识和东亚内部知识的交流(《“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7期)。李建民写过牛黄相关的文章(《丝路上的牛黄药物交流史》,《中医药文化》,2018年第1期)。李贞德近年关注当归新的用药,他不仅从性别上来讨论,也讨论当归进入朝鲜半岛的时间,甚至他德国的药厂档案里面找得到了当归的使用(《女人要药考——当归的医疗文化史试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7,第88卷第3期)。此外,在澳门工作的白雅诗(BeatrizPuenteBallesteros)关注到底野迦和巧克力这种出现在清代宫廷里面的食物,从耶稣会士的角度来讨论的涉及药物和食物的交流("ChocolateinChina:InterweavingCulturalHistoriesofanImperfectlyConnectedWorld,"inTranslationatWork:ChineseMedicineintheFirstGlobalAge,ed.HaroldJ.Cook,BrillRodopi,2020)。陈明还补充一部季羡林先生的《糖史》两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这本书虽然并没有提全球史,也没有提很多新的理论,但这本书大量讨论了糖的技术,糖从药物变成食物过程,以及与印度、波斯和欧洲的联系,还包括中国制糖技术流传到印度的过程,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糖这个简单物品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文化交流史的东西。最后,陈明提出了几个问题给大家来思考,并请作为传统学问的名與物里面涉及到知识的结构贸易和文化相遇,很多本草书中只有“名”没有“物”,很多外来物逐渐消失了,但是与它知识相关的“名”还在。在以全球史的视域进行讨论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或者说,如何避免哪些问题?药物、食物研究与贸易史、日常生活史等的边际在什么地方?新的研究与传统的药物史、食物史研究有哪些不同?从事相关研究需要加强哪些理论修养?梁其姿就上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她认为选择物相关的研究题目时要发掘这个物的重要性,最好选择一个能广泛地呈现社会变化的物,这样的物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能力才足够强。以《甜与权力》(SweetnessandPower:ThePlaceofSugarinModernHistory,NewYork:VikingPenguin,1985)和季羡林先生的《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为例,糖是我们日常都会用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物,糖这个物里面所隐含的技术面和社会面都很丰富。研究这样的一个物才会有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在选择题目时,基本上是看你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跟历史上有密切相关的主题,不只是研究食物跟药物,关于任何的题目都是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选择物的研究对象时一定要把这个物和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联系起来。避免同质化的“内卷”研究,而是应该往外去生发出更广泛的话题。对于相关的理论修养,materialculture的研究包括了技术史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此外一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十分重要。因为文字记载通常都是隔离层,从田野调查里面常常会得到在书本文献里面得不到的知识。现场有学生提问到的国人研究中医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梁其姿认为两者主要在选题上不同,由于中国医学在中国本身占主流地位,所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医学的时不太担心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人看的问题。但是在西方,选题这一方面都要比较考究,他们必须要选一个题目在西方医学史的领域里面也会感兴趣的话题。中西两方做法都各有利弊,在中国研究医学史方面的论文在资料和背景知识方面有一定的水准,而西方学者在把握史料方面不一定很全面,研究成果可能有时会以偏盖全。另外一方面,西方学者他们选题的时候就会很在意题目是一定要能与同行研究进行对话,或作比较,这样才能在学术界受到重视,占有一席之地。针对中西医对脚气病的认识有何不同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脚气病”,很多现代人误解为皮肤病,梁其姿明确到,她提到的脚气病指的是四肢神经末梢受损害的病,重者影响心脏病发引致死亡。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只是吃白米所引起的,这个解释实际上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在,因为在19世纪20世纪初,发明了有将含有营养素的米糠完全磨掉把米礳得很白的机器。西方医生认为吃米为主的亚洲人因此容易得脚气病。他们以为所有亚洲人都能吃到白米,又或者除了米,他们什么也吃不到。这实际上是完全是误解,亚洲人不可能只吃白米,而一般人其实也吃不到昂贵的白米,而是有糠的米。这是对不同种族的主食的一种文化偏见。欧洲人研究脚气病的实验是用鸡来进行的,他们用白米来喂鸡,然后发现这些鸡的脚都软掉了,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实际上缺乏维生素B1的原因很多,酗酒、过劳与不良生活习惯,营养不良都是原因,所以当时欧洲医生只是针对白米这个原因是一个很偏颇的解释。十九、二十世纪交接之际,中国人一般仍认为湿热是主要的病因,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脚气病是由东南亚传入的,一些人因此也不愿意到东南亚谋生,是为了不染这个病。至于近代营养知识进入中国后,对于疾病疗愈观念有何具体影响,梁其姿认为这个需要看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总觉得中国人普遍缺乏营养,因为中国人吃蔬菜很多吃肉很少。但是中国人是不是真的营养不良,我们无从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随着当时西方营养观念进入中国,国人也接受了新的营养观念。这个观念的改变其实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时孙中山和一些革命家也不觉得中国人一定要吃很多肉,补充大豆的蛋白质就足够,那时中国还是大豆生产最多的国家。1920年代开始,从美国留学返国的学者才大力提出动物蛋白质的优越性,此后肉食蛋白质的吸收才成为健康的重要指标。而今天无论西方人或亚洲人,我们对吃肉来吸收蛋白质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过多的肉食已被视为有害,无论对身体或环境,而素食也不一定让人营养不良,今天素肉已成为时尚的健康食品。责任编辑:于淑娟校对:施鋆